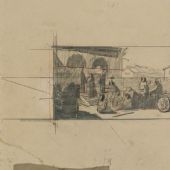在建国十七年(1949-1966)间,经过向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术“一边倒”的学习,接受延安文艺座谈会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思想的洗礼,发扬解放区美术创作的革命传统和基本经验,美术界逐步形成一套现实主义油画创作的方法,其步骤大约如下:
确定主题后深入生活(或者,在深入生活中确定主题);
围绕主题,搜集素材,形成构思性草图;
根据构思性草图、素材,必要时辅以模特儿写生,以更深入地塑造形象,形成未来油画作品的造型与构图基础——素描习作和作品素描稿;
在素描习作和作品素描稿的基础上——有时是同时——形成油画色彩稿,必要时辅以油画色彩写生,以明确作品总体和局部的色彩关系,最终创作完成油画作品。
50、60年代面世的许多主题油画,莫不出于这样的创作过程。其它如新年画、新国画、雕塑、版画等不同画种的主题性创作,亦与此大同小异,只是在第四步——作品载体方面——因存在专业区别而对色彩要求程度不一。在这样的创作过程中,每一幅主题创作背后,几乎都有少则几张、十几张,多则成本成册的速写、素描、色彩写生以及各种角度的构思性草图。有时作者为了真实再现创作构思,甚至还会像拍电影一样力所能及地搭建一个“实景”,以便于深入研究特定场景下的构图、色彩与人物关系。不过,在“唯创作论”普遍存在于专业创作与教学实践时,人们往往看重的是创作的最终成果,也就是最终完成的那件作品,而对酝酿作品的草图、习作的艺术价值不够重视,这导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到今天),国家文博机关没有有意识地收藏这一部分,美术史研究者也较少有意识地研究这一部分,画家中除了有心者或恋旧者外,也大多没有特别有意识地保存这一部分,即使是个人画展也多不陈列这一部分。长久以往,时过境迁,原本一套丰富、跌宕、完整的艺术叙述,往往只留下或者只公开“作品”这一艺术叙述的最后章节。除个别作者因为创作出了引起社会反响的作品,被权威刊物约稿总结创作经验,才得以有机会披露创作酝酿、构思、实施过程,并附带发表两、三幅草图习作之外,绝大多数作品(其中不乏许多优秀作品)的草图习作,则在创作完成、展览、出版后,被作者尘封、散佚或者毁损了,以致外界并不了解该作品的创作详情。从这个层面上讲,建国以来诸多优秀美术创作的收藏与研究都极不完整,是残缺的。王式廓的《血衣》却有些例外,而正是这一例外的存在,更反衬出美术界对建国以来诸多优秀美术作品的创作过程的搜集与研究,实在太过贫乏。
从目前所见资料来看,王式廓(1911-1973)从1950年开始构思反映农村“土改”的油画创作,到1973年5月23日去世前还在为这件作品搜集形象与色彩素材,前后历时二十多年,是一件在新中国美术创作史上历时最长而终未实现画家本来愿望的作品。该创作原计划以油画形式完成,1957年,作品尚在素描草图、习作阶段时,就被中国美协机关刊物《美术》重点报道,不仅在封面和内页选刊习作和草图,而且还专门发表了评论文章。一件作品,尚未完成即受到如此关注,这在《美术》杂志编辑史上迄今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如果深入地看,不难发现,《美术》的报道并不仅仅在于对王式廓创作实践的肯定,而有更为现实的需要,这就是,在建国以来,美术宣传口非常需要选择一个“有力的例证”,在思想和实践上清理对创作的非无产阶级、非现实主义的“混乱认识”,为美术工作者学习和掌握“正确的创作方法”提供借鉴,以引导美术创作的现实主义发展。细言之,就是要以具体的创作实践为例——苏联画家的或者是中国画家的,当然最好是中国画家的创作,以便能够更亲切直观地为广大美术工作者打开理解现实主义主题创作的基本主旨与实现方法的窗户,学习如何“通过一瞬间的可视形象来表现人物思想感情的发展趋向,深刻地揭示人物的复杂的精神状态”以及“复杂社会关系和阶级矛盾与冲突”。因此,《血衣》尽管还是草图和习作,但却因极符合这种现实需要而被宣传口历史地选择和记录下来,并且宣传口的这种记录将随着《血衣》的发展而升级,由此不仅使《血衣》罕见地成为新中国美术创作与出版史上比较完整地公开草图、习作等创作过程的作品,而且成为建构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步骤的范本。
王式廓在构思创作《血衣》同步完成的《井冈山会师》(1957)、《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1958)等油画作品,尽管也画了不少草图、习作,却没有享有像《血衣》那样草图、习作被关注的待遇,当时的观众与读者只是在展览、刊物、独幅印刷品或邮票中见过这两件油画作品,至于相关草图、习作,则要等到1982年人民美术出版社为缅怀和展示王式廓一生艺术创作成就、出版《王式廓画集》时才公开。同样是王式廓本人创作,为何《血衣》的草图、习作受到关注,而《井冈山会师》、《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则只看创作结果,原因应该只有一个:相对于《血衣》,这两件作品在思想深度和表现深度上都显平淡,和同类题材的表现拉不开距离,虽然它们在完成度上都比《血衣》前进了一步,画成了油画,但其创作过程却不足以成为图释现实主义艺术创作方法与步骤的最佳范本。
1959年是建国十周年,也是王式廓非常忙碌的一年。十年大庆的需要以及美术界对这件“概括了一个时代生活的纪念碑式的巨大作品”的期待,要求王式廓在比较紧的时间内尽快将《血衣》全幅创作完成,若按原计划画油画,时间显然不够,因此要在国庆节前完成创作任务,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将为创作油画《血衣》积累的素描草稿、习作,顺势转换升级为完整的素描创作。打定主意后的王式廓为此经过数月努力,为刚落成的中国革命博物馆赶制出了素描《血衣》。素描《血衣》的诞生,虽然具有这种赶庆典的即时性,而且素描也不是王式廓希翼的最终艺术面貌,但由于作者长期深入生活、搜集素材的准备,以及深入细致的创作性习作研究,《血衣》中的人物形象早已胸有成竹,所以王式廓画起来得心应手,几乎一气呵成。在保证创作任务完成的同时,素描《血衣》以极其朴素但非常符合作品情感基调的黑白灰语言,极具戏剧性冲突效果却又葆有浓郁的现实生活气息的构图处理和人物塑造,使新中国美术创作第一次实现了以素描表现重大主题,较为完整地体现了素描作为现实主义创作方式的艺术价值。由此,素描《血衣》迅即成为宣传的重点和“大家谈”的中心。王式廓的创作经验总结《“血衣”创作过程中接触到的几个问题》,即刻在中央美术学院校刊《美术研究》1960年第一期发表,人民美术出版社在1961、1962年相继出版《血衣》和《王式廓素描集》,中国美术馆在1963年收藏了王式廓34幅《血衣》的创作性习作,《美术》在1963-1964年“大家谈”栏目发表对《血衣》评价的数篇争鸣文章,在这一系列涉及总结、出版、收藏、争论的过程中,使《血衣》的草图、习作、创作,在事实上成为现实主义美术创作的教科书,今天五十开外的这一批艺术家中,有多少不是看着王式廓的素描入门的呢?也就是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现实主义”与“素描艺术”进一步成为认识和评论王式廓艺术的基点,从中逐步建构起王式廓在新中国美术史上“人民(农民)画家”、“素描巨匠”的地位。
素描《血衣》完成并取得广泛的社会反响后,王式廓并未能借势而发、一鼓作气创作完成油画《血衣》。一来,他因病休养两年,无力顾及创作,实际上也错过了60年代初期文艺大发展的那一段好时光,此后由于众所周知的社会运动,延缓了他创作油画《血衣》的时间;二来,油画创作毕竟难度更高,作为大型油画创作——王式廓设想将油画《血衣》画成真人等大的巨幅油画——对创作条件、身体条件、艺术经营等各方面的要求也更高,王式廓为此也只能等待着。据相关记载,王式廓1969年形成油画《血衣》草图,1973年4月应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之约,为创作油画《血衣》赴河南写生,在一个月的时间里,王式廓画了74幅油画和素描,严格按照现实主义油画创作的准备要求,用色彩语言熟悉着生活、体会着形象、充实着构思,所做的正是本文开篇谈到的第四步工作。在河南写生期间,他每日凌晨四点起身,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在花甲之年如此拼命,是他深深地感到创作油画《血衣》的“序幕不能太长了,现在已经太长了。”遗憾的是,5月22日王式廓脑溢血突发,手握画笔倒在了他正在写生的农民兄弟面前,翌日与世长辞,享年62岁。正式创作油画《血衣》的序曲刚刚奏响即成哀乐,得其帮助、受其恩泽的师生亲朋,只有通过1969年的油画草图和1973年河南写生的那批绝笔习作,想象着油画《血衣》的面貌,寄托着对王式廓的哀思。
以下所谈的《血衣》草图、素描65幅,是王式廓创作素描《血衣》前完成和积累的那一部分,依据画面信息及信息的完整度和工率度,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整体构思性草图,共9幅(图3、12、39、42、43、54、60、61、64);
第二类:局部形象构思性草图,共24幅(图1、2、4、5、7、8、9、10、13、14、15、16、17、18、19、20、21、22、23、31、32、33、48、51);
第三类:创作性习作,共32幅(图6、11、24、25、26、、27、28、29、30、34、35、36、37、38、40、41、44、45、46、47、49、50、52、53、55、56、57、58、59、62、63、65)。
以上三类,较为系统地展示了王式廓《血衣》构思和创作过程,形象地演示了本文开篇所说的现实主义创作前三步,其中除个别草图和习作曾在有关出版物发表外,均未曾公开。因此,若将其与有关出版物已公开发表的部分联系起来阅读,无疑将会从整体上进一步体会王式廓对待构图和形象由粗到精、由浅到深的加工演变过程。
例如,将第一类整体构思性草图,与1982年人民美术出版社《王式廓画集》发表的图65-68(以下标为RM)联系起来看,一个“血衣”情节从无到有的寻找过程,一个围绕“血衣”情节展开的群像组织过程,非常完整地被勾勒出来。
图3和RM67是尚未出现血衣情节的草图,但较之RM67“《血衣》草图(第一稿)”来说,图3或许是更早的一件酝酿构思的草图,虽有讲述者、记录者和倾听者,但意图体现很不明确,看不出是在开会讲政策还是在控诉斗地主。RM67则不一样,斗争意图明显加重,场景开始明确为一处老建筑的石阶前,主体人物之一——被打致残的受迫害者首先明确出现在草图中。在以后出现“血衣”情节的草图中,可以看到,虽然残废者的形象屡有变化,但其构思基本未变。不过,场景构思一度发生较大变化,如图54中,王式廓将场景置换为村中的一片空场,试图让手持血衣的人站在高桌上,让群情激奋的群众围拢着地主大声质问,但不久王式廓就放弃了这一想法,重新恢复到原有的场景构思内,寻找着最佳的场景透视与黑白关系(如图39(即RM66)、图64),同时开始有意识地控制表面上的激愤张扬,抑制振臂高呼、激烈斗争的气氛,在整体上倾向于愤懑痛苦而又内敛压抑的艺术基调(如RM68、图61、RM65)。
在整体构思和基调逐渐成熟的过程中,局部形象也从构思发展为具体的形象。例如图23(即RM78)是王式廓对被打致残的农民形象的最初构想,该草图图文并茂,细读其中提示性文字,可以看到王式廓对这位农民的年龄、体态、表情、情绪在构思上已比较完整,在日后完成的素描《血衣》中,这位男青年的艺术形象与草图提示性文字完全对应。另如图45(即RM97)是对地主形象进行研究的一张比较完整的素描作品,虽然王式廓最终没有在创作中选取从这一角度刻画地主,但什么是王式廓说的创作性习作,由此可得到解答,即为创作而做的各个角度甚至各个局部的充分而深入的研究。相对于总体创作来讲,它是富有研究色彩的习作,但因其研究之充分深入,其本身也就构成了独幅创作。这也就是为什么王式廓的《血衣》在总体上是一件完整的艺术创作,在局部形象上也是一件一件可以单独欣赏和发表的艺术创作的原因。
综上可见,创作上一丝不苟的王式廓从不放松创作的每一环节,在从构思草图到作品完成的整个创作过程中,他就像一个下地的农民期待丰收一样,对垄地、翻地、播种、施肥、除草、灌溉、收割的每一步都做得那么到位、讲究、专注。“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实在就是王式廓的艺术实践和创作过程的真实写照。在延安时期,王式廓就是开荒生产的“劳动模范”,在新中国现实主义美术创作上,他也无愧于这个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