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技术到艺术
14世纪90年代,意大利画家和理论家切尼诺·德·安德烈·琴尼尼(Cennino d’Andrea Cennini,约1360-1427年前)撰写了一本《画匠手册》(The Craftsman’s Handbook),成为留存至今的较早系统记录绘画材料和作画技术步骤的重要文献。“画匠”(或“工匠”)的称呼透露出那个时代对于艺术家身份的普遍观点,今天我们概念中的艺术家在那个时代被视为是与理发匠、金匠一样的人,这是自古希腊以来的悠久传统,就如“艺术”最初的本意是“技术”一样。然而,也正是在文艺复兴的时代,“工匠”的身份开始逐渐地向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艺术家”转变。
 图1 阿尔布雷希特·丢勒:《描画鲁特琴》,1525年发表于其《测量手册》中,木刻,画中画家所用的“透视器”类似于阿尔贝蒂的纱屏
图1 阿尔布雷希特·丢勒:《描画鲁特琴》,1525年发表于其《测量手册》中,木刻,画中画家所用的“透视器”类似于阿尔贝蒂的纱屏
在《画匠手册》中,琴尼尼表述了对于艺术起源和地位的重新认识,从技术的起源进入对艺术的认识:“(创世纪之后)种种不同的技艺接踵而来,其中一些曾经且仍然比另一些更为精巧,它们彼此间不都是平等的,其中最高超的是科学。之后,由科学派生出一门技艺,此技艺须依靠科学而以手运作,可称此技艺为绘画。绘画必须具有想象力和灵巧的手,能显现我们从未见过的事物,赋予其自然元素的外观,并用手使之固定,令人相信无中生有。由此理由,可排列绘画于第二行列,紧随科学,与诗歌同等声誉。”[1]琴尼尼的观点代表了文艺复兴时代有知识、有文化的艺术家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同,这种认同将艺术家(主要指画家和雕塑家)的地位开始从一般意义上的工匠技艺中提升了出来,艺术开始变得不同寻常,而其独特之处就在于引文中所说的“想象力和灵巧的手”:前者可以理解为创造力,而后者则可理解为纯熟的技艺,这两者共同构成了一个艺术家之所以能够超越于一般工匠所应具有的特质,这是从“技术”到“艺术”得以实现飞跃的必要条件,是“画匠”与“画家”之间的最大差异。
 图2 列奥纳多•达芬奇:《博士来拜》(透视草图),1481年,纸本钢笔、墨水,163x290 mm,佛罗伦萨乌菲奇美术馆藏
图2 列奥纳多•达芬奇:《博士来拜》(透视草图),1481年,纸本钢笔、墨水,163x290 mm,佛罗伦萨乌菲奇美术馆藏
自文艺复兴以来,大量的艺术家借助光学仪器进行绘画如今已经是艺术史上公认的事实,在大卫·霍克尼的考察中,他将光学器材进入绘画的年代假定在了1430年左右,因为通过考据,正是在这个时间段,佛兰德斯出现了借助光学仪器进行绘画的技术,而此后,这样的新式技术开始流传开来,也因而使绘画的风格变成了光学仪器折射后的那种图像风格。[2]更为系统化的技术是关于透视的技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作家、建筑师、艺术理论家阿尔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1404-1472)1435年完成的《论绘画》系统记录和介绍了那个时代所能掌握的透视技术及相关绘画辅助工具,比如非常实用的透视构图辅助法:阿尔贝蒂方格,以及简单且容易操作的工具:纱屏。这些技术和工具让绘画的逼真描绘变得相对简单,甚至是没有系统训练的初学者都可以借助这样的技术获得一个非常完美的图像,尽管在今天看来,这样的事实多少有点消解我们惯常概念中笼罩在大师们头上的神圣的光环,然而,真正伟大的人物却并不仅仅满足于依靠工具和技术进行创作。以达·芬奇为例,达·芬奇是那个时代佛罗伦萨艺术家韦罗基奥画室中培养出来的佼佼者,他早期的作品中就显示出了非常纯熟的透视技术,但是,现藏于乌菲齐美术馆的一件作于1481年的草图《博士来拜》却显示出了他对于标准透视法的某些有意改变。这张画中显而易见地使用了阿尔贝蒂方格来描绘画面场景的透视关系,这种表面看上去无懈可击的精美技艺,在细节上却存在不少问题,这一问题通过画面中的人物的安排与场景的关系透露出来,显示出艺术家在画中更关心的并不是借用了透视技术再现了一个看上去逼真的场景。根据美术史家的分析,事实上,约作于1495-98年间的《最后的晚餐》是他最后一幅运用透视法画出的作品,在此之后,他的画作中再未用过几何透视法。[3]达·芬奇在掌握了更为便捷的技术之后却并不沉迷于技术本身,而是很快地转向了其他更值得研究的领域,这是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超越技术的一个典型的明证。
1550年,被誉为“美术史之父”的乔尔乔·瓦萨里出版了他的《大艺术家传》,将在他所建立的艺术史系统中处于巅峰的米开朗基罗称之为“天才”:“在已经去世和仍然活着的艺术家中,天才的米开朗基罗使所有的人黯然失色,他不是在一种艺术中,而是在所有三种艺术中都出类拔萃。他不仅胜过那些几乎征服自然的艺术家,而且甚至胜过那些无疑已经征服了自然的最杰出的古代艺术家。米开朗基罗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战胜了自然本身,而自然所生成的事物,无论多么具有挑战性,多么非凡,都没有一样是他那富有灵感的天才凭着应用能力、构图、艺术技巧、判断力和优雅所不能轻而易举地超越。”[4]瓦萨里建立的艺术史树立了一个伟大艺术家的标准,他真正将艺术家与工匠区分了出来,并在艺术与自然的差异中提升了艺术的价值。艺术成为了超越自然(真实再现)的一种创造性活动,而艺术作品则是“想象力和灵巧的手”的智慧结晶,这或许是艺术超越技术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特质。
回顾从技术到艺术在观念史上的发展历程和那些有名的例证有助于我们看清究竟什么是艺术创作中的“匠心”,伟大的艺术家从来都是技术上的杰出者,但又从来都不是技术的迷恋者,那些之所以能被称之为“天才”的伟大人物是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得精湛技术的同时又迅速摆脱技术诱惑的冒险家,是真正以艺术的方式为技术立法的人,这是艺术之匠心与工匠之匠心的最大差异。
图像时代的冲击
艺术的发展从未脱离技术的发展,每一个重要的技术的出现,都会带来艺术史上或大或小的震动,比如文艺复兴时代系统的透视技术及其相伴的一系列绘画工具的出现就极大地改变了艺术的面貌。在近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对于艺术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摄影技术的出现了,这一技术的发明和发展直接导致了我们今天所称之为的“图像时代”的出现。
1839年,法国国家科学院宣告了摄影技术的诞生,紧接着艺术世界就感受到了摄影所带来的威胁。绘画的危机感来源于绘画图像真实性的被剥夺,照片的出现取代了此前绘画作为图像记录的传统功能,自文艺复兴以来对于绘画真实再现技术的迷恋到此时开始变得毫无意义,无怪乎当时著名的学院派画家保罗·德拉罗什也会发出这样的哀叹:“从今天起,绘画死亡了。”伴随着摄影技术的不断完善和照相机的更新换代,照相机的镜头开始取代了人的自然的眼睛,艺术家们也偷偷摸摸地开始借助照片来作画,安格尔、库尔贝、马奈、德加等等这些大师都或多或少地使用过照片,照片对于绘画所提供的便利恰恰成为了绘画自身危机的明证。但是,照片在带给绘画危机的同时,也迫使绘画去寻找自我,这种自我的反思已经在那个时代的批评之声中有所反映。
波德莱尔在1859年的沙龙评论中已经明确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对摄影的批判在本质上是对那个时代绘画“堕落”的痛心。“由于摄影业成了一切平庸的画家的庇护所,他们不是过于缺乏才能,就是过于懒惰不能结束学业,所以,这种普遍的迷恋不仅具有盲目和愚昧的色彩,而且也具有复仇的色彩。……但是我确信,摄影这种进步,如同一切纯粹物质上的进步一样,错误的应用极大地加剧了本来已经很少的法国的艺术天才的贫困化。”[5]波德莱尔看到,技术的进步所造成的对真实再现功能的瞬间实现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而绘画对于真实性的迷恋已经成为了一种“盲目和愚昧”,那些曾经通过勤学苦练才能够获得的造型能力在照片出现之后变得更加轻而易举,于是对于平庸的画家而言,终于能够具备这样的能力成为了一种具有“复仇色彩”的自我陶醉。然而,此时艺术的历史轨道已经不可归复地改变了,这样的写实除了自欺欺人之外,还有什么意义呢?因此天才带来绘画的改变成为了一种时代的渴望。
 图3 埃德加·德加:《晨浴》,188790,纸上色粉画,706x433mm
图3 埃德加·德加:《晨浴》,188790,纸上色粉画,706x433mm
伴随着摄影技术快速发展的正好是印象派的兴起,也正是从印象派开始在改变绘画的形式倾向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循着印象派开启的道路,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现代主义的形式革命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趋势。但是,人们对于绘画真实的迷恋始终没有被完全超越,在挥之不去的工匠习气和人类观看的本能习惯的作用下,欣赏视觉的真实仍然是最为主要的大众趣味,只不过在当代社会的各种包装诱惑之下,这种真实变得越来越肤浅和庸俗了。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波德莱尔感慨,摄影——在此作为真实图像的代名词——“将凭借着它在群众的愚蠢中找到的天然的盟友而立刻彻底地排挤或腐蚀艺术。”对于绘画而言,这一点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完全改变。
然而,照片对于绘画的冲击仅仅是刚刚开始,伴随着图像技术的加速度发展,照片、电影、电视这些更加系统化和真实的图像呈现方式开始不断地充斥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从刚开始摄影被以绘画这样的传统艺术形式所看轻和排斥,到绘画不由自主地利用和接纳照片,再到照片、电影开始被视为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成为多种艺术创作方式的一种,这期间绘画经历了逐渐走向纯化和极端的现代主义形式变革。尽管,绘画的形式一直在不断的变化和革新中改变,但是作为最基本的在二维空间中从事图像制作的手工技术却没有从本质上发生技术变革,绘画的改变开始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绘画之外的对象,从最根本的方面来说是依赖于观念,甚至对于本体论而言也是如此,因为即使讨论形式本身的价值也是一种观念化的表述。
图像时代的特征就在于图像本身充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对于一个对象或是外部世界的接触、了解和认识都是通过图像的手段来实现的,图像正在越来越多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而这种改变同时也是在不断地规定和塑造着我们的经验、我们的习惯以及我们自身,当代的绘画也是图像所生产和塑造着的绘画。从19世纪的那些大师们开始遮遮掩掩地使用照片,到现代主义时期绘画努力地逃离照片、再到后现代时期绘画故意地模仿和挪用照片,图像对于绘画的塑造和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这仅仅只是图像塑造方式的一种表现形式;事实上,对于那些试图保持“纯净”,宣称传承和延续传统的绘画而言,也依然是在努力从前人的图像中复制或重新组合出自己的图像,毕竟图像本身就是其获得传统资源的重要方式。
 图4 安迪·沃霍尔:《花》,1964年,纸上丝网印版画,耶鲁大学美术馆收藏
图4 安迪·沃霍尔:《花》,1964年,纸上丝网印版画,耶鲁大学美术馆收藏
如果说,当摄影技术出现时是绘画开始面临危机的时候,那么到当代,这种危机依然没有改变,当我们开始不断地去关注和探讨当代绘画的问题时,就意味着这种危机感的强化。当代的绘画在两个方面走向了越来越细致的层面:一方面是传承了现代主义的精神,将自我的表现、个人的感觉、习惯和手性通过绘画的方式记录下来,尽管我们可以说,绘画从来都是个人化的,但当代的绘画在个人化的层面上变得越来越富有差异性,如果说习惯上我们观看绘画的方式是从风格入手的话,那么当前我们对于绘画的观看则是从个人出发,当代绘画开始越来越成为一种私人化的东西,可以是自我的情感、自我的体验,也可以是个人的趣味,或者仅仅只是一种自我的娱乐;另一方面,当代的绘画开始越来越多地从技术化的角度寻求突破。早期的典型如:安迪·沃霍尔的“工厂”生产出的大量丝网版画、以新现实主义和抽象表现主义为代表的“行动”所留下的图像痕迹被作为绘画来展出,以及超级写实主义那种格子里填色的技术等等。来源于几何抽象的那种“机械般的”绘画方法也是一种常见的方式,画家的描绘成为了一种机械的工作,按照设计好的图像描绘规范的或是任意的图像,从而构成一种观念的表达方式,今天的不少冷抽象绘画都采取这种方法,尽管图像千差万别,但本质是一样的。此外,借助电脑打印技术或直接利用电脑进行绘画也是一种被广泛采用的方式。比如:今天的画家惯常使用的将草图打印在画布上再进行描绘的方法、使用电子设备如手写板或者iPad来绘画,或者直接利用计算机的算法建模形成图像,再将其转化到画布上等等。更有甚者,绘画成为了一种科学实验的手段——人工智能绘画,比如:前不久谷歌公司开发的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够创作出艺术的图像,这一技术的发展不同于早期机器人绘画的那种僵化的固定机械动作造成的图像,而是使用了人工神经网络来“创作”,这是人工智能发展的一项重要的变革。当然,这些变化所带来的问题也是极其复杂的,它涉及到我们应该如何重新去理解和定义艺术,如何理解技术带来的艺术变革,或者技术自身的艺术性问题,或许,在不久的未来,机器智能将会对绘画构成新一轮的重大影响。
技术时代的绘画
回顾观念史上艺术从技术的脱离、图像时代新的技术媒介对绘画的挑战和影响,以及当代最新的关于绘画创作的多种方式,似乎凸显出了一个问题:绘画在当下正面临着一个十分尴尬的局面。或许,在每个技术转折的历史时期,绘画都会面临着相应的转型的难题,但是在当代,伴随着艺术形式和媒介多样化使用的爆炸式增长,绘画在整体的艺术世界中所占据的份额不可改变地缩小了,对于艺术史而言,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当前国外的美术学院,包括在那些具有悠久历史、曾经显赫一时的美术学院中,传统的绘画训练——尤其是写实的造型训练已经变得非常稀少了,绘画仅仅是作为多元化的艺术表现手法的一种在学院里面保留,按照艺术创作的不同需要被选用,而不像一百多年前那样占据统治地位。绘画在今天所面临的这种状况并不是孤立现象,而是任何一种文化形态在相应历史时期都要面临变化的普遍状况,就像油画技术、各种版画技术也都是在特定的时期被发明出来一样,当新的技术开始作用于艺术创作的时候,传统媒介遭受冲击是必然的结果,这一点,就像在网络和电子传媒技术大量普及和日益变得便捷化的今天,纸质媒体所面临的冲击一样。这是在当下的技术时代绘画所面临的整体境遇。
 图5 达明•赫斯特在伦敦的高古轩画廊站在他的一张“色点绘画”前面,2011年
图5 达明•赫斯特在伦敦的高古轩画廊站在他的一张“色点绘画”前面,2011年
当代的绘画还面临着另一个层面的困境,就是上文所提到的当代绘画开始越来越多地从技术化的角度寻求突破,然而,技术化的突破却更多地依赖于观念,这一点导致了当代的绘画走向了一种内部的自我消解,因为不少依赖于观念的绘画恰恰都是反绘画的。从现代主义的逻辑开始,形式的不断革新求变是绘画的一个整体趋势,到马列维奇或者极少主义艺术家那里的时候,绘画已经在媒介的纯化中走向了尽头,画面成为了媒介自身的呈现,绘画也就成为了物品,这是绘画自我消解的一个典型方式。从蒙德里安的那种规整的几何抽象,到埃尔斯沃兹·凯利的色域绘画,再到达明·赫斯特的色点绘画,绘画不仅转化为了一种设计,更重要的是绘画性的丧失,当代绘画的反绘画性恰好是针对绘画技艺的自我消解。应该说,当绘画开始依赖于观念的支撑,开始通过既定的、可大量复制的图像被艺术家不断地“生产”出来的时候,以及当绘画仅仅是作为带有设计性的图样被制造出来的时候,正是绘画自我的丧失,但是,我们要追问的是,究竟什么又是绘画性呢?按照沃尔夫林的说法,绘画性就在于涂绘,英文中的“绘画”(painting)也就是“涂绘、涂抹”的意思,所以,涂绘性似乎成为了当代绘画的一个出口,这也是为什么在今天的绘画中,坏画成为了一个热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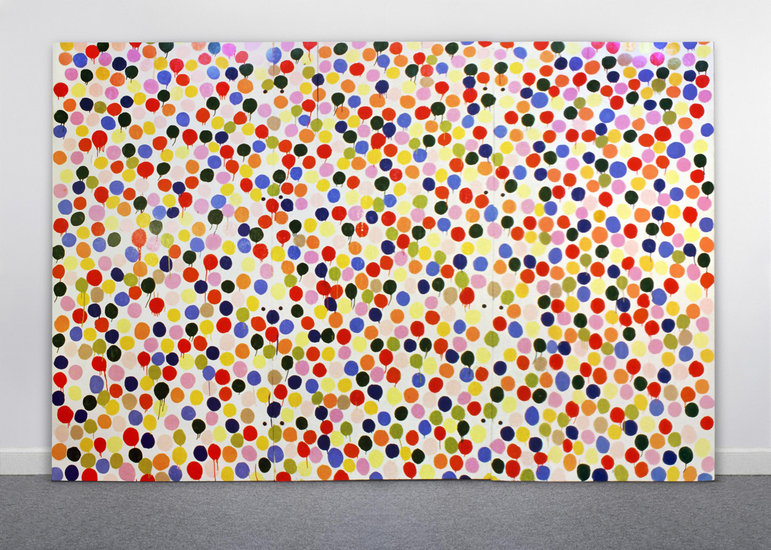
图6 达明•赫斯特:《色点绘画》,1986年,板上家用玻璃,2438x3658mm
坏画(Bad Painting)的概念最早来源于1960年代意大利的贫困艺术,来自于意大利批评家对于贫困艺术的讨论,1978年,在美国的新美术馆举办了一个名为“坏画”的展览,这个展览后来成为了坏画正式进入艺术领域的一个标志。[6]坏画继承了贫困艺术的精神诉求,要求艺术要回归自然、回归泥土、回归身体,对绘画而言,这就意味着艺术家要按照自己最为真实的本能去作画,在画面中呈现出那种脱离了制度和理性、脱离了规则和限制的状态。坏画的这种诉求,恰好从最大程度上满足了“涂绘性”的要求,表现那种在绘画的规则秩序出现之前的人的绘画状态,而涂绘的意义就在于记录下了身体最为原初的体验和感觉,成为了人的本质的流露和对象化。然而,真正的坏画实际上又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当代的画家往往都是被学院训练所规范过、经过制度和规则裁剪过的画家,能真正做到脱离这些秩序并找寻到自我的艺术家微乎其微。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当下对于坏画的关注实际上也成为了一种技术性的选择,是在绘画所面临的当代境遇中寻求绘画自身突破所采取的一种策略。
承认在当前日新月异的技术时代中绘画面临强大的冲击并不应成为禁忌,因为对于绘画的理解并不能通过盲目的自我陶醉——尤其是那种沉迷于个人技术的自我陶醉——而变得深刻,重要的是应该理解这种影响的方式、探讨绘画本质性的特质,并清理当前关于绘画价值的观念,由此才能为未来的发展提供思想性的参考。关于影响绘画的方式以及绘画本质性的特质这两方面上文已经做了探讨,在此有必要进一步清理当前我们对于绘画的价值认同问题。
关于艺术作品的价值,瓦尔特·本雅明在其著作《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膜拜价值”与“展示价值”,这或许可以作为我们清理关于绘画价值问题的一个出发点。本雅明将艺术史描述为艺术品在“膜拜价值”与“展示价值”两极概念之间的交互地推重,他的论述是从艺术作品发端于巫术的祭祀活动出发来讨论的,并分析了早期的那种膜拜价值要求人们隐匿艺术作品,此后,“随着单个艺术活动从膜拜这个母腹中的解放,其产品便增添了展示机会。”[7]这里所说的“膜拜价值”是从巫术艺术和宗教艺术的角度来阐述的,但是艺术品的膜拜在观念上却始终是处于变动中的。从早期的巫术崇拜、宗教祭拜,到文艺复兴时代尤其是瓦萨里所建立的对于天才艺术家的崇拜,再到现代主义的英雄崇拜,再到后现代时期裹挟着各种文化语境所包装起来的艺术明星的崇拜,伴随着艺术家地位的逐步提升,对于作品的膜拜也与日俱增。然而,膜拜却并不都是为才华与技术而折服,膜拜的异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尤其是当代社会中,艺术品的膜拜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了商业膜拜的幌子,成了投资和变现的工具。消费社会的逻辑导致的艺术作品的膜拜价值的异化也是当代绘画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当然,这与绘画自身的物质性特征有关,因为从本质上来说,绘画本身作为一种艺术创作的手段并不构成价值,只不过由于收藏的便利性。绘画一直以来都是艺术市场上的宠儿,但这本身却与艺术价值无关,更为重要的问题时,伴随着对资本和利润的无休止追逐,商业的异化会消解和束缚艺术的创造性使之成为纯粹的工具性生产。当然,绘画的膜拜价值并不仅仅反映在商业的异化方面,同时也与情感有密切的关系,对于当代画家而言,绘画作为一门具有悠久历史和传统的创作方式,同时具有了文化遗产的特性,因此,对于绘画的感情,成为了一种“对遥远的或已消逝的爱进行缅怀的膜拜”,成为了维护个人情感乃至捍卫个人价值的一种象征。
 图7 大卫•霍克尼:《冬天的木材》,2009年,由15张油画合成
图7 大卫•霍克尼:《冬天的木材》,2009年,由15张油画合成
然而,无论是上述哪种方式,绘画的膜拜价值其实也并不直接构成绘画自身的价值,对于当代绘画而言,展示价值成为了最为重要的价值体现方面,但也只是作为艺术创作中可供选择的众多表现方式的一种,在合适的情况下和个人趣味及习惯的作用下,发挥相应的艺术表现力。当下艺术创作中最为普遍的情况是,绘画开始越来越多地和其他各种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段如:雕塑、装置、影像等共同构成一件作品,以达到更为丰富和立体的效果。
每个时代都会出现伟大的艺术,但在艺术史上却也很少(除了瓦萨里这样的少数人物)有哪个艺术理论家会宣称自己时代的艺术已经达到了高峰,当我们今天在不断地讨论和批评当代的艺术所面临的问题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积极地推进当下艺术的发展。当波德莱尔在批判他那个时代艺术的时候说到:“艺术一天天地减少对自己的尊重,匍匐在外部的真实面前,画家也变得越来越倾向于画他之所见,而非他之所梦。”[8]这里所强调的“梦”或许是每个时代都有的理想,它指代的是人类在无意识中自由的创造性产物,这种状态下的产物是迷人的,因为它连接了过去、当下与不可知(因而也是未来)的状态,因此,就艺术的发展而言,“梦”成为了一个关于艺术发展的隐喻。每个关心艺术的人都有一个关于艺术的未来之梦,无论是何种样貌的梦,今天的艺术家能够做到真诚地表现自己的梦就已是不易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梦幻是一种幸福,表现梦幻的东西是一种光荣。”
注释:
[1] 切尼诺·德·琴尼尼:《画匠手册》,戴海鹰节译,转引自:《世界美术》,2015年第4期,第68页。
[2] 可参见:大卫·霍克尼:《隐秘的知识——重新发现西方绘画大师的失传技艺》,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
[3] 关于达·芬奇透视法的分析可参考法国美术史家达尼埃尔·阿拉斯的研究。参见:(法)达尼埃尔·阿拉斯:《绘画史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
[4] 乔尔乔·瓦萨里:《著名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家名人传·第三部分序言》,参见:(意大利)乔尔乔·瓦萨里:《意大利艺苑名人传·巨人的时代》,刘耀春、毕玉、朱莉译,湖北美术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引文译法参考其他版本略有不同。
[5] (法)夏尔·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第402页。
[6] 在国内最早介绍坏画的文章参见:易英:《坏画探源》,收入:易英著:《原创的危机》,河北美术出版社,2010年7月第1版。
[7](德)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第61页。
[8] (法)夏尔·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第40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