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从技术对于社会和文化形态的改变和塑造这一问题入手,探讨了当代新媒体艺术的表征及相关问题。本文第一部分通过讨论麦克卢汉和波斯曼等学者的相关理论,清理了新技术对于社会文化形态可能带来的塑造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第二部分探讨了计算机时代新媒体艺术发展的几个特征,其中着重分析了跨码性这一特征,并提出跨码性的实现主要通过三种类型的界面体现出来:基础界面、增强界面、集成界面,这三种不同的界面也基本可以代表当前新媒体艺术发展的形态特征。本文最后通过娱乐性和技术恐惧这两个交叉视角探讨了当代新媒体艺术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并基于技术漂迁理论将其视为一种可变的文化形态,而其对于艺术史发展形态所可能带来的美学特性的改变也将是未来有待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技术;文化塑造;计算机;新媒体艺术;表征;跨码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尼尔·波斯曼
麦克卢汉在其著作中指出了媒介对于日常生活的改变与塑造作用,并且强调了真正发挥作用的因素并非媒介所传播的内容,而是媒介的技术形式,正是后者塑造了人类感知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循着这条研究道路,以尼尔·波斯曼为代表的第二代媒介环境学派的学者对媒介形式发挥作用的方式进行了进一步研究,这既包括研究内容上的细化,也包括时间上的推进以及对于新出现的文化状况的思考。与此同时,伴随着新一代学者研究的推进,媒介技术自身的形式及其改变社会的方式与深度也在发生着变化,技术本身不仅仅在以日益迅疾的加速度发生着更新换代,同时其对于社会和文化形态的改变和塑造也在以更为深刻和隐秘的方式展开。甚至出现了“在观念的残垣断壁之中,只剩下一个可以相信的东西——技术。”[1]当波斯曼在其著作中以这种方式来表述技术的时候,这是对技术的一种反讽,但也是在意识到文化面临技术侵蚀的严重问题时发出的警世危言,他的警示不是针对技术本身,而是指向了人类自身。
文化的技术侵蚀
如果说,以《机器新娘》、《理解媒介》等为代表的著作显示的是麦克卢汉对20世纪50-60年代的技术发展程度及其对于社会的影响所做出的判断,那么尼尔·波斯曼则以其三部重要作品揭示了20世纪80-90年代的技术进程及其文化影响。波斯曼从1982年出版的《童年的消逝》就开始批判电视文化对于成人和儿童界线的消解,提出以电视为媒介的大众传媒打破了由印刷文化所建立起来的成人和儿童之间的文化界限,从而造成了关于“成人化的儿童”与“童年”消逝的一系列问题。1985年出版的《娱乐至死》进一步通过追溯媒介发展的历史批判了电视对读写能力的消解,在波斯曼看来,印刷时代已然走向没落,而电视时代正蓬勃发展,它“从根本上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还包括其表达方式,更为重要的是,它让一切公众话语都以娱乐的方式呈现,从而让人类成为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在前两部著作的基础上,1992年出版的《技术垄断》是波斯曼对于技术与文化之间关系更为系统和更加激进的讨论。波斯曼总结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三种陆续出现的文化形态:工具使用文化阶段、技术统治文化阶段,以及技术垄断文化阶段,在其最终阶段面临的问题就是文化向技术投降。从波斯曼的理论进路来看,他还是沿着麦克卢汉的思路推进的,他们的著作围绕的一个核心问题都是关于电视文化对于印刷文化的冲击,而其中被改变和塑造的“当下的”文化基本上属于印刷文化。波斯曼那个激进的表述:“文化向技术投降”并非意味着文化的失败,而是指文化在两个大的方面被技术所影响。一方面是在一些传统的文化形态和与之相关的符号层面,伴随着新技术的运用,这些文化形态和符号系统逐渐消退以致消逝;另一方面指的是技术对于当下文化形态的塑造,这种塑造在波斯曼那里毋宁说是“异化”,即技术对于当下文化形态的异化,当然与之相伴的同样也是人的异化。因此,“文化向技术投降”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述为“人自身向技术投降”,这一现象在他探讨“机器意识形态”问题的时候着重讨论的两个例子——医疗技术垄断和计算机技术垄断——中得到了典型的体现。
但是,在这一思维逻辑中,值得探讨的问题在于,人和技术之间的关系恰好无法被割裂乃至对立起来,按照哲学人类学的观点(比如阿诺德·盖伦),人类正是凭借着技术的发明才获得了自身的发展或进化,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进化,同时也是社会形态的进化,就文化本身而言,(按照麦克卢汉及波斯曼的观点)事实上也是特定技术塑造的结果,正如印刷术塑造了印刷文化形态一样,新的技术也将塑造新的文化形态。因此,假如因为新的技术及相关媒介打破了旧的技术所建构的文化形态,比如波斯曼所关注的电视文化对于印刷文化的消解,便据此对新的技术加以批判乃至否定的话,便会带来一个悖论:即人类文化一方面依靠技术得以塑造,而与此同时又拒绝技术的塑造,因为技术是一个不断在更新换代的变动进程,而固守特定时期的文化形态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以静止乃至保守的文化观念去抵制不断变化的历史现实,而处于历史的当下,永远也无法断言当下的文化和即将被改变和塑造而形成的新文化形态究竟孰优孰劣。当然,无论是麦克卢汉还是波斯曼,都未曾直接陷入印刷文化的保守主义,他们也不吝肯定新的技术在某些方面所带来的文化改变是有益的,在麦克卢汉那里甚至大体上持乐观的态度,而在波斯曼的著作中他更关注的问题是技术改变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尤其是对这种负面效应的强调一度被认为是他看待新技术的唯一观点,这也是为何其著作饱受争议的原因。事实上,无论技术对人类社会的文化形态产生正面的塑造还是负面的影响,如果以绝对化的表述过分强调这种影响力的话,都会被视为典型的技术决定论,正如雷蒙德·威廉斯对麦克卢汉的批判一样,假如在探讨的过程中忽视了特定的社会和历史文化情境,便会出现重大的理论缺陷。因此,在探讨新技术的社会塑型作用的时候,引入特定的社会和历史文化情境的考虑是必要的,从这一视角出发,重新去阅读麦克卢汉和波斯曼的著作,就能够超越技术决定论激进的思维定式,从他们的思考中获得启示。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当代艺术的技术实践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情境,不仅仅艺术本身的性质决定了这一情境可能具有不同于社会情境中技术实际应用的功能背景,同时,艺术语言与媒介的独特历史语境也将新技术的艺术实践带入到了一种超越技术决定论的艺术情境中,也就是说艺术的实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内在于艺术史的话语体系,而非日常生活中真正的大众媒介(如波斯曼所批判的电视媒介),在这种情况下,波斯曼等人对于新技术的批判视角与当代艺术的新技术实践便构成了一种互文性关系。这一方面可以为艺术的当下实践提供技术所带来的文化塑型的社会语境,对于当下的文化所可能带来的改变而言,这些新的艺术实践既是隐喻也是表征;而对于当代艺术的技术实践而言,技术的批判话语提供了一种视角,可以去审视作为当下前卫文化表征的当代艺术实践,在这些多样化的实践中,艺术可以是新技术的热情拥护者,可以是如波斯曼那样的激烈批判者,同时也可能构成批判的对象,成为如同电视文化那样的大众娱乐媒介本身。
尽管在不少学者看来波斯曼多有激进之嫌,但是在他的著作中,尤其是在对新技术的敏锐意识和批判性思考中,对理解当下文化形态的变动依然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性意义。在这些著作出版三十多年后,当我们今天重新去审视这些思想的时候,也会发现麦克卢汉和波斯曼所说的很多情况已经变成了当下的现实,而在跳出技术决定论激进思维的情况下,以艺术的实践作为观察对象探讨在刚刚过去的这几十年文化形态发生变动的那些具体情况,也能够意识到,新技术所带来的艺术实践既有正向的刺激和改造,也有异化的趋势。
新技术给当代艺术的实践带来正向的刺激和改造现在几乎已经构成了一种共识,在艺术史的框架中,新媒体艺术史已经越来越作为一种重要的类型备受关注,假如追溯从摄影开始的媒体艺术发展的历程,就会发现新技术对于艺术发展形态的巨大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有几个重要的技术节点,也相应地对应着新的艺术形态在艺术史上的出现:摄影、录像、电视、计算机、互联网。在这些技术形态中,计算机是非常特别的,它不同于其他的技术形式,而是发展成了一种基础技术形态,也就是说,计算机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机器,比如我们通常所说的一台电脑,更是一种可以覆盖其他技术形式的基础性技术工具,且已经深入到了当代社会的各个领域之中,在今天看来,其对于社会的改造和塑型无论从广度和深度来看,都远远地超越了电视。但是,在艺术史的视野中,除了那些从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出发展开的攻击和否定之外,关于新技术给当代艺术实践所带来的异化趋势的讨论,却并没有在事实上深入展开,因此,有必要借助于波斯曼的技术批判理论去清理相关的问题。当波斯曼在批判电视文化所带来的文化异化问题的时候,计算机的影响力正在逐步上升,而他在《技术垄断》中也已经意识到了其强大的潜力。然而,波斯曼当时对于计算机的认识还是有限的,当他在“机器意识形态:计算机技术垄断”中谈论这一问题的时候,事实上当时的计算机还处在家用普及的上升期,其功能和应用程度还很有限。但今天看来,计算机所带来的改变或许才是真正地做到了“童年的消逝”和“娱乐至死”,甚至其影响比这些还要更加强烈和深刻。
计算机时代新媒体艺术的表征
在《技术垄断》中,波斯曼敏锐地意识到了新技术变革的一个重要特征:计算机的出现和快速发展给社会文化形态带来的深刻影响。他在书中探讨了两种类型的技术垄断:医疗技术垄断和计算机技术垄断,实际上这两种都属于技术理性发展到极端的一种表征——对于数字化(精确计量与计算)的依赖和崇拜,而数字化的技术呈现在今天最为重要的技术形式就是计算机,包括医疗技术在内的人类社会的各种技术形态都逐步被整合进了计算机技术之中,甚至在不少学者看来,计算机已经渗透进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便是计算机所具有的“普适性”特征。根据波斯曼的观察,其包括以下两个方面:“(1)计算机的用途多得数不清;(2)计算机整合进了其他机器之中,因此我们难以将计算机技术推进的理念从其他机器里分离出来。”[2]波斯曼所观察到的现象正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中技术发展最为重要的现象:微型计算机的快速发展和普及。从1977年第一代家用电脑“苹果II”(Apple II)上市开始,整个1980年代都是家用微型计算机快速市场化和普及化的重要时期,到80年代末,美国的中产阶级家庭已经基本普及了微型计算机(家用电脑)。为何这种微型计算机如此受欢迎呢?除了市场营销之类的因素之外,最主要的特征就在于其强大的集成化功能,比如:在微型计算机强势崛起的同时,一度对游戏机产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原因就在于对于消费者而言,既能够玩游戏,还能够运行办公软件的电脑显然是更好的选择。

1977年第一代家用电脑“苹果II”
伴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今天的计算机所具有的功能和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的地位已经和波斯曼所观察到的1980年代的情况发生了天壤之别,在其可能具有的功能与如何发挥作用这两个层面上,计算机都已经产生了飞跃性的发展。首先,就计算机的功能来看,假如说波斯曼当年的说法还略有夸张的话,那么今天看来确实是“多得数不清”。我们不必从计算机本身出发去细数功能,只需要大致思考一下今天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否还有不涉及计算机应用的领域?这样的例子似乎少之又少,由此可见,计算机本身已经渗入了人类社会现代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其次,就其发挥作用的方式来看,今天的计算机已经成为了一种基础性的技术手段,可以说,不仅无法将其从机器中分离出来,也无法将其从人类活动所涉及到的一系列关系中分离出来,不仅包括人生命的诞生和延续(比如医疗技术),也包括人的思维方式和各种类型的社会交往。在关于媒介的讨论中,计算机所发挥的作用也远远超越了其他媒介的影响,如果说,传统媒介的影响仅仅是集中在某一个单一的环节或要素的话,那么计算机所具有的影响力则是全方位的:
印刷的发明仅仅影响了文化传播中的媒体分发这一个环节。同样,摄影的发明也仅仅影响了文化传播中的静态影像这一种类型。然而,计算机媒体革命不仅影响了传播的所有阶段,包括信息的获取、操纵、存储和分发;也影响了所有的媒体类型,包括文本、静态影像、运动影像、声音和空间建构。[3]
在列夫·马诺维奇的这一表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与印刷、摄影、录像、电视等媒介相比,计算机所具有的强大影响力,它几乎已经将媒介发挥作用所涉及到的一切容纳其中,无怪乎今天的计算机——具体来说,一个网络化的可编程机——已经成为了“当代最重要、最广泛的媒介”,甚至在我看来已经成为了一种当代媒介的“元媒介”。而之所以将其称之为“元媒介”,就在于计算机深刻地改变了媒介的属性,它使得“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了这种情况:媒介的技术基础设施不再与其表面特征具有同源性。”[4]比如:一张印刷版画上的图像就是作品所要表现的视觉图像、留声机唱片上的沟槽代表了人类理解声音的频率、早期照片的胶片是对实际拍摄对象光线的记录等等,这些传统媒介都是与人类的感觉直接关联的,而计算机的储存与处理机制则与人类的实际感觉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其真正所处理的是讯息,而不是信息,前者仅仅是对人类视觉、听觉的一种符号化记录和模拟,而后者才是人们所能接收和释读的内容。马诺维奇将基于计算机技术的新媒体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层面:
“文化层面”和“计算机层面”。文化层面的例子包括百科全书与短篇故事、故事与情节、组合关系与视点、拟态与情感宣泄、喜剧与悲剧;计算机层面的例子包括进程与数据包(通过网络传输的数据包)、分类与匹配、函数与变量、计算机语言与数据结构。[5]
也就是说,文化层面的内容相当于媒介传播的信息层面,是关于媒介传播的内容方面。而计算机层面则全然不同,涉及到以数字化形态呈现的一系列讯息的技术处理问题。基于这两个不同的层面,他进而对计算机的文化塑型作用做出了说明:
由于新媒体由计算机创建,通过计算机分发,使用计算机存储并且归档,计算机的逻辑极大地影响了媒体的传统文化逻辑,换句话说,计算机层面会影响到文化层面。计算机可以模拟世界,呈现数据,允许人工操作。所有计算机程序背后都有一套主要操作(例如搜索、匹配、分类、筛选),人机交互界面也具有一套惯例——总之,我们可以称之为计算机的本体论、认识论和语用学。这些都影响着新媒体的文化层面,包括新媒体的组织形式、新出现的类型,以及新媒体的内容。[6]
在这段说明中,马诺维奇所说的计算机层面对于文化层面的影响,与麦克卢汉及波斯曼所强调的媒介本身的性质和结构对于社会文化的塑型作用这一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但是,每个人的侧重点是非常不同的。麦克卢汉强调了媒介本身对人的知觉的延伸,波斯曼主要集中批判了媒介所带来的异化效果,而马诺维奇则是清理了基于计算机的新媒体所具有的诸多特征。对于当代艺术的新技术实践而言,通过这些不同学者的观点所提供的互文性关系去理解当下艺术发展的问题,便成为了理解今天的新媒体艺术特征及问题的有效的参考。
 本杰明·弗兰西斯·拉波斯基 《电子抽象4号》 1956年 计算机、阴极管示波器、胶卷、灯泡
本杰明·弗兰西斯·拉波斯基 《电子抽象4号》 1956年 计算机、阴极管示波器、胶卷、灯泡
伴随着计算机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日益深入和明显的影响,以及当代艺术不断开展的各种新技术的艺术实践,新的艺术形式对于艺术语言和艺术史本身都已经产生了影响。“计算机艺术”(Computer Art)这一术语描述的就是那些基于计算机技术的新艺术实践,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计算机图形技术的发展,这一术语捕捉到了较早呈现出的直接由计算机影响艺术创作的那些现象,实际上其源头还可以往前追溯到50年代本杰明·弗兰西斯·拉波斯基(Benjamin Francis Laposky)的“电子抽象”。[7]但是今天看来“计算机艺术”这个表述已经多少有些过时了,原因在于这一描述显得过于空泛,因为不仅仅计算机已经渗透进各个艺术的门类,比如绘画、雕塑、设计等多种传统艺术门类的创作都会使用到计算机,而且,计算机本身也衍生出多样化的技术形态,比如图像编辑、3D打印、网络传输、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等,每一种类型的技术形态都可能会激发新的艺术创作实践类型,因此,今天的这类艺术实践往往更倾向于通过相对明确的技术形态给艺术实践命名,如网络艺术、人工智能艺术、生物艺术等等,而这些艺术形态习惯上都被统称为“新媒体艺术”。
针对新媒体马诺维奇总结出了五个特征:数值化呈现、模块化、自动化、多变性、跨码性[8],并指出这些特征“更像是计算机化的过程中,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9]按照马诺维奇的说法,这五个特征是按照逻辑顺序来排列的,并且“后三个法则建立在前两个法则的基础之上”。“数值化呈现”和“模块化”这两个特征更多地是基于计算机技术形态本身做出的总结,展现出技术操作“物质性”的一面。比如一幅图像必须通过数值化的“定义”方式才能够被计算机识别和读取,在对其进行处理的时候也依赖于数值算法。同时,在处理这个对象的时候,计算机需要通过模块化对其进行采样,比如像素、色值、脚本等等,并基于诸如子程序、算法函数等这样结构化的计算机程序进行处理。虽然,“数值化呈现”和“模块化”这两个特征揭示了计算机技术如何得以运用和具体操作的本质性特征,但就是文化层面而言,理解其文化塑型的方式却依然比较模糊。除非是那些能够真正使用编程语言进行创作的艺术家,可以通过这两种方式去进行创作,但对于今天的大部分艺术创作者而言,这些问题都不是直接影响其创作的要素。在前两个特征的基础上,基于程度的变动和模块的可替换和可修改特性,“自动化”和“多变性”都比较好理解。但其中真正重要的是最后一个特征“跨码性”,正是在这个角度,计算机层面和文化层面直接相遇并产生影响。
马诺维奇所说的计算机层面对于文化层面的影响就是从跨码性这个视角展开的:“在新媒体的术语里,‘跨码’就是将一个事物转换成另一种格式。”[10]从技术层面上看,基于数值化呈现特征的跨码类似于编码和解码的过程,但在文化层面上,跨码性呈现的是一个状态,一方面它连接了计算机的技术处理层面,另一方面它又与人类的感官体验——文化层面——直接相关,这是最具意义多变性的一个节点。比如一幅数字图像,它可以通过文件格式、像素、色值等要素被计算机识别,这属于计算机层面的“语言”,同时又可以通过呈现出来的图像体量、色彩感觉、图像内容等与人类的知觉发生关系,这属于文化层面的意义交互。因此,跨码性是意义转换和生成的一个不确定的场所。不仅如此,其形态也是多样化的,无论是一幅虚拟的数字图像、一个用于呈现图像的实体屏幕、或者是一个由灯光音效等共同作用生成的多媒体沉浸式场域,都是跨码得以实现的载体——一个象征性界面的不同呈现方式,而这个交互的界面成为了今天新媒体艺术的一种典型表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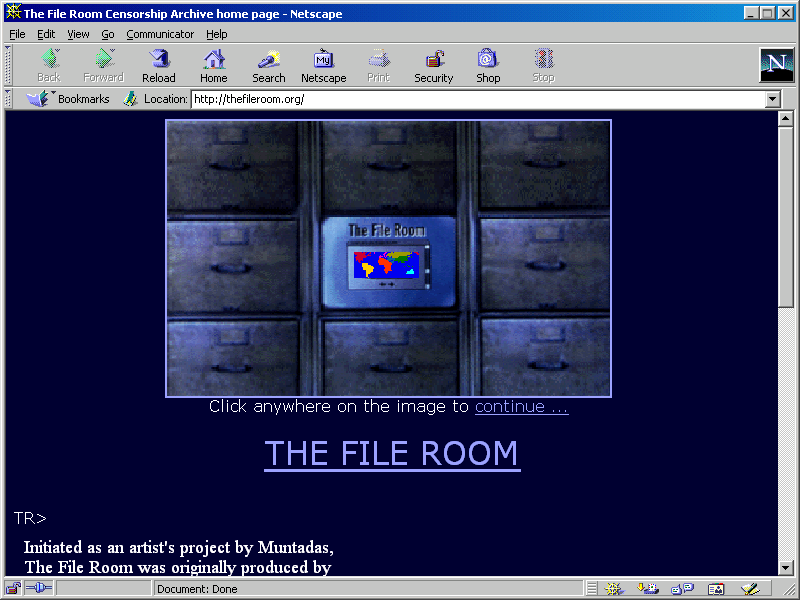
安东尼•蒙塔达斯《档案室》 1994年 登陆网址:https://thefileroom.rog/
在今天对于新媒体艺术的思考中,尤其是探讨其与艺术史之间的关系问题的时候,有学者将其总结为以下几种类型:作为可触界面的数字化图像、交互作用、数据库、视觉浸润、多媒体集合、连接性、移动性、扩张的真实。[11]如果将这些特点与新媒体自身的特点进行对比的时候,就会发现,实际上这些特点都仅仅是对已经出现的一些艺术实践的特征进行的描述,并且显得琐碎甚至重叠。假如基于上文所述的新媒体自身的那五个特征进行整合的话,可以将其总结为以下几种类型:首先,“数据库”是基于“数值化呈现”,这方面比较好理解,比如传统媒介的数据化就是一种典型方式,这方面的作品中最为经典的就是安东尼•蒙塔达斯的《档案室》。除此之外,其他几个特征都是经由“跨码”得以衍生出来的:“作为可触界面的数字化图像”、“交互作用”——这些属于最为基础的跨码界面,比如一个触摸屏;“视觉浸润”、“多媒体集合”、“扩张的真实”——这些特征都是从视觉仿真出发,进而发展到一种综合性感官刺激,但依然依赖于一个跨码界面,只不过此时的这个界面可能是一个虚拟空间(比如通过VR制作),或是一个融合了现实和虚拟景观的场域(比如通过MR制作),这种类型的跨码界面可以称之为增强界面;最后一种跨码的方式略显复杂,“连接性”和“移动性”这两个特征侧重于空间与运动,实际上这一方向早在20世纪60年代的偶发艺术实践中就尝试过,比如1966年玛塔·米努辛的多媒体艺术项目《同时性的同时性》。[12]但要通过新媒体技术实现这一点的话,其跨码界面可能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界面,而是由两个以及更多的界面构成,这些不同的界面通过模块化集成而成生一种集成界面,由于模块化的可替换性和可修改性特征,就会实现艺术作品的连接性和移动性。由此,可以对计算机时代新媒体艺术的跨码性特征进行总结,基于作品不同的表达方式和呈现形态,跨码性主要通过三种类型的界面体现出来:基础界面、增强界面、集成界面,而这三种不同的界面也基本可以代表当前新媒体艺术发展的形态特征。

玛塔·米努辛 《同时性的同时性》 1966年 多媒体行为表演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托尔夸托·迪·特拉学院
但是,上文仅仅是基于新媒体艺术的形态特征进行的清理,而关于新媒体艺术所具有的文化学意义,在不同学者那里却有着不同的认识。有的将其理解为一个自足的世界:“新媒体艺术定义了一个完全独立的‘艺术世界’,既不同于当代艺术的世界也不同于其他‘艺术世界’。想要充分理解,对新媒体艺术的定义就必须基于社会学而不是技术。”[13]也有的将其理解为一种混杂的艺术形式、一种跨学科的微观实践;还有的将其理解为为未来进行艺术媒介探索的实验;抑或是将其视为在“艺术世界”之外出现的一些“艺术的”发展,即通常是由那些并不将自己首先视为艺术家的研究者、科学家或者积极分子们展开的实践。无论如何,事实上目前对其文化学形态进行定义还为时过早,因为关于新媒体的艺术实践还处于不断的发展和变动的过程中,但是正如上文所讨论过的,新媒体艺术的形态深深地根植于新媒体技术自身的结构性特征,因此既需要从技术层面进行思考,同时也需要从文化和社会层面进行评估,只有通过这种双向关照,才能对其表征进行深入的理解。出于这一考虑,也许还有必要重新再回到波斯曼,从他关于技术的文化塑型思想出发,哪怕是从那些略显偏激的思想中,可以获得关于当前新媒体艺术发展某些问题的启示。
娱乐、恐惧与技术漂迁
在《娱乐至死》中,波斯曼做出了一种预言式的假设:“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14]前者指代的是在《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庄》中所表现的那种监狱式的文化,而后者则指《美丽新世界》的寓言:在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社会中,也许最容易造成毁灭和控制的就是娱乐本身。而波斯曼正是通过电视文化显露出来的问题,揭示了娱乐可能具有的破坏性的力量:
思考无法在电视上得到很好的表现,这一点电视导演们很早以前就发现了。在思考过程中,观众没有东西可看。思考不是表演艺术,而电视需要的是表演艺术。美国广播公司展示给我们的是原本具有高超语言驾驭能力和政治见解的人现在屈服于电视媒介,致力于表演水平的提高而不是表达他们的思想。……最后,大家为这些表演鼓掌,这也是一个好的电视节目所希望得到的,也就是说,它需要的是掌声,而不是反思。[15]
波斯曼的这段话生动地说明了,大众传媒的屏幕所需要是表演,而不是思考,换句话说,在这种大众传媒结构泛滥的情况下,思考本身在事实上被取代了,因而也就被压制和消解了。即使是那些表面上选择严肃话题的谈话节目,也必须在有限的展示时间中将注意力集中在表达和形象的营造上,视觉和听觉的表象成为了最终的目的。所以他说:“在电视上,话语是通过视觉形象进行的,也就是说,电视上会话的表现形式是形象而不是语言。”[16]从《娱乐至死》到《技术垄断》,波斯曼所探讨和关注的对象也从电视转向了计算机,或许正是他意识到了计算机的快速发展所能发挥的作用和可能带来的改变远远地超越了电视,因此提出了关于“技术垄断”看法:“任何技术都能够代替我们思考问题,这就是技术垄断论的基本原理之一。……所谓技术垄断论就是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都臣服于技艺和技术的统治。”[17]这里所表达的意思就是人的感觉和智性被技术性——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非人性的秩序和规则——所压迫、裹挟乃至控制,甚至当逐步进入到这种状况的时候尚且不自知,这其实是最为可怕的境况,这也正是《美丽新世界》中所呈现的那个“文明社会”的恐怖之处。
但是,技术究竟是如何实现这种文化“异化”的呢?这其中可能包含两种情况:一种是类似于《一九八四》和《美丽新世界》这样的寓言,有一个统治阶级的存在,正是基于统治阶级对于技术的掌控才带来了文明的异化,这是一种形式的技术垄断;而另一种形式则可能基于技术自身,根据兰登·温纳的思想,如果从技术的政治哲学视野出发就可以看出技术可能具有的自主性力量:
所有技术的首要功能——及其效用的直接条件——是使一组原料或一种特定的人类活动形成一个明确的、人为的形态。换句话说,它将结构赋予它所适用的对象。……一项技术性操作根据你参与其间的程度来决定你能做些什么。如果操作是成功的,我们就可以说技术决定了结果。这并不意味着技术或其结果是完全固定或不可改变的。这实际上表明的是,通过征服无序状态以及将形式强加给事物,技术取得了成功。[18]

朱莉娅·谢尔 《朱莉娅安保II》 1989-90年 摄像机、监视器
温纳在这里所谈论的技术不仅仅包括一个装置(机器)、一种技法,同时也可能是一个(人机互动的)技术组织或技术性操作,技术的实现依赖于操作,而操作本身决定了人所能发挥作用的程度。但是即便是成功的操作也并不意味着人对于技术百分之百的控制,因为无论是成功的操作或者失败的操作都不是一个确定的结果,因为在此之外还可能产生许多其他出乎意料的结果。由于熵增实际上是一种自发的过程,因此,要提高技术将形式强加给事物的可能性就需要有更多的条件保证,这就意味着技术系统需要不断地完善自身——扩展规模和更新换代。但是,也正是伴随着技术革新的速度和深度在增加,最终结果的“不确定”和“非故意”也变得愈加明显了,比如:杀虫剂和除草剂给生物圈带来的意外影响,或是信息技术的进步让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反而提高了,以及无处不在的监控在有效监管的同时也触及到个人隐私和自由的问题等等,这方面朱莉娅·谢尔的《朱莉娅安保II》或《总是相伴》等作品就是对监控的意识形态问题做出反思的典型之作。这些在技术设定结果之外产生的出乎意料的效果这就是所谓的“技术漂迁”问题,所以温纳说“技术做到的总比我们想要得到的多。”[19]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也构成了另一种类型的技术垄断。

朱莉娅·谢尔 《总是相伴》(选自“监视床”系列) 1994年 多媒体装置
由于技术漂迁所产生的结果是不确定的,因此假如要讨论当代新媒体艺术的实践成果的话,或许依旧无法明确究竟会产生哪种具体的结果,就效用而言其中可能有积极的结果,也会有消极结果。但是如果循着波斯曼的思路,即娱乐可能带来的文化异化问题,便可以将视角集中起来,因为恰恰这种异化也是一种意料之外的漂迁。在上文所讨论过的基于计算机技术的新媒体艺术的表征中,一个最为重要的特点是由跨码性所带来的交互界面。从艺术史的视野出发,交互界面的出现所带来的最为直接的效果就是提供了观众与作品互动的便利,而传统艺术史中的观众,此时已经不再是观看者,而成为了参与者,这意味着:一方面单一的视觉拓展为多重感觉,加入了听觉、触觉等等;而另一方面,交互本身激发了观众的参与意识,这使得作品的“欣赏”从传统上单纯的观看(思考)转向身体参与的活动,作品变成了可触摸、可控制甚至可修改的形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作品的接受变成了一种趣味性的活动。
综合感官的刺激和深度参与带来的趣味性这两点是否说明:当代的新媒体技术赋予了艺术作品一种典型的娱乐化特征?当然艺术本身也可以是娱乐的,在艺术史上一个特定的题材也自然会带来娱乐性的效果,比如关于酒神巴库斯的题材,但新媒体技术所带来的仿真与沉浸式体验似乎已经大大强化和放大了这种娱乐属性。在今天的艺术世界中那些备受欢迎的新媒体艺术团队和个人所提供的作品就体现出了这种特征,这些作品常以制造宏大的视觉景观为目的,展览变成了灯光和投影秀,热火朝天的排队体验和各种亲子互动环节让美术馆恍如游乐场,而且这类作品还经常作为新艺术的代表在各类庆典活动上亮相,成为了各种官方和商业活动备受欢迎的必备节目。在波斯曼看来,娱乐表面上是人性的张扬和自由释放,实际上却是一种麻醉剂,假如这就是当代新媒体艺术的发展方向的话,便如波斯曼所言“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波斯曼是这么描述媒介形式对文化的影响的:
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能最终控制文化。……我相信,某个文化中交流的媒介对于这个文化精神重心和物质重心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媒介,……它们更像是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20]
新媒体艺术的媒介形式确实具备某些“偏好的内容”,即上文所述的综合感官的刺激和深度参与性,而这些内容也确实在今天构成了塑造当代社会文化景观的一种因素。但是,这个跨码的界面却并不是一个二元论框架的产物,也就是说:“数字界面,……既是它所包含和修正的关系的一个活跃的组成部分,也是构成互动新媒体装置的系统的一个深层纠缠的部分。这一系统包括艺术家、观者/参与者、界面和交互的新媒体装置本身。”[21]这就意味着,“偏好的内容”也未必会具有固定的意义,所以,对于新媒体艺术的理解可能会涉及到多重关系,既具有一种混杂性的特质,也掺杂着主体性的问题,同时,在技术快速更迭的影响下,短暂和不确定性也构成了其特征,所有这些都让界面本身作为新媒体艺术的表征变得可塑和多义。
就艺术史发展的形态而言,新媒体艺术的实践是否会改变艺术自身的美学属性呢?至少从当前来看艺术的形态确乎发生了变化,但究竟美学特性如何定义还有待探讨。有学者认为这一发展趋势已然形成了一种新的美学:基于界面的数字美学,并且提出“数字美学……就是媒介化的时间经验。”[22]但是由于媒介化的方式还在快速更迭,因此,关于数字美学的面貌也还在形成之中。就当下的艺术实践而言,大部分新媒体艺术对于“时间经验”的媒体化处理可能从形态上来看还是多少存在一些文化“异化”的问题,即带有典型的娱乐性特征,但或许娱乐也未必是一个确定的意义,也可能发生“漂移的漂移”产生意料之外的效果,成为了解构僵化秩序、传统美学惯例、既定思维及艺术范式并激发未来艺术创造力的起点,正如温纳所言:“当技术后果的最终范围既没有被预料到也未受到控制的时候,它是最富成效的。”[23]
注:
[1][美]尼尔·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何道宽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4月第1版,第61页。
[2]同上,第117页。
[3][俄]列夫·马诺维奇,《新媒体的语言》,贵州人民出版社,车琳译,2020年8月第1版,第19-20页。
[4][美]W.J.T.米歇尔、[美]马克·B.N.汉森,《媒介研究批评术语集》,肖腊梅、胡晓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第1版,第142页。
[5][俄]列夫·马诺维奇,《新媒体的语言》,贵州人民出版社,车琳译,2020年8月第1版,第123页。
[6]同上。
[7]参见:赵炎,“从画布到屏幕——作为抽象艺术的数字图像与计算机艺术的发端”,《艺术评论》,2019年第2期。
[8]“跨码”一词在书中原文为“Transcoding”,中文语境也译为“转码”或“代码转换”,本文中暂用中译本译法“跨码”。
[9][俄]列夫·马诺维奇,《新媒体的语言》,贵州人民出版社,车琳译,2020年8月第1版,第27页。
[10]同上,第46页。
[11]参见:[意]安东内拉·斯布里利,“新媒体与艺术史:1990-2010”,赵炎 译,《艺术评论》,2012年第8期。
[12]参见:赵炎,“经验拓展的场域——偶发艺术与新媒体实验”,《世界美术》,2018年第1期。
[13]Domenico Quaranta, Beyond New Media Art, Link Editions, Brescia 2013.P35-36.
[14][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5月第1版,第185页。
[15]同上,第109-110页。
[16]同上,第8页。
[17][美]尼尔·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何道宽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4月第1版,第57-58页。
[18][美]兰登·温纳:《自主性技术》,杨海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第65页。
[19]同上,第84页。
[20] [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5月第1版,第10-11页。
[21]Phaedra Shanbaum, The Digital Interface and New Media Art Installations, Routledge, 2020, P.34.
[22]Sean Cubitt. “Aesthetics of the Digital”, in A Companion to Digital Art, ed. Christiane Paul (London:John Wiley&Sons, 2016), P.266.
[23][美]兰登·温纳:《自主性技术》,杨海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第8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