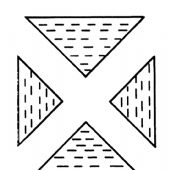内容摘要:本文以20世纪50-60年代的偶发艺术作为讨论的对象,通过追溯和分析其观念的起源和逻辑线索,重新回顾在偶发艺术影响下出现的那些新媒体艺术实践,将其与后来的新媒体艺术发展路径建立起了一种结构性的联系,梳理出一条相对清晰的新媒体艺术发展的观念逻辑线索,展示出了新媒体艺术发展历程中那个重要的开创性时期和颇有意味的历史横断面。
关键词:偶发艺术、经验、新媒体
在西方当代艺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20世纪50-60年代是一个爆发期,无论是艺术的形态还是观念在这个时期都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展,当我们追溯新媒体艺术发展的历史线索之时,从这个时间段出发,能够清理出多条线索,比如:白南准的影像实验、约翰·凯奇、罗伯特·劳申柏和肯宁汉等人的表演、安迪·沃霍尔的实验电影、布鲁斯·瑙曼的行为影像及霓虹灯装置……所有这些都可以被认为是新媒体艺术发展历程中具有开创性意义的重要实践。其开创性首先在于媒介与手法的变化,上述艺术实践都采用了新的媒体设备和表现方式,比如对于录像、电视、灯光、投影等新媒体设备的使用和剧场化的表演,这些不同于传统的新颖方式让这些艺术实践在当时成为新前卫的代表。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关注当时到底出现了何种艺术思潮?经典的艺术形式,尤其是那个时代最具主导性地位的架上绘画为何突然失去了吸引力?为何当时有如此多的艺术家积极投身于那些看起来奇奇怪怪的实验?是何种新的思想在迅速传播和发酵,在其鼓动之下将年轻一代的艺术家吸引到了这个试验场之中?
在20世纪50-60年代的那些艺术实践中,偶发艺术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艺术思潮,与当时其他“正统的”艺术实践相比,偶发艺术具有的一个最为独特的属性就是在形态上明确提出了艺术的日常生活化和公众参与性,而其他的前卫艺术实践则主要侧重于观念的实验,无论是行为(比如工作室表演)、实验电影、还是早期影像装置,主导作品生成的首先是观念的实验,但是无论艺术家的目的是传达何种观念,作品本身的呈现方式带给观众的始终是一个视觉样本,行为艺术的影像化就突显出了这一问题。视觉优先的原则来自深厚的艺术史传统,也是视觉艺术的本质属性,然而,从偶发艺术开始明确提出的那些方向,却在一定程度上转换了视觉优先的问题,预示了未来艺术发展可能出现的新方向,为后来的新媒体艺术发展将艺术的道路从单纯的视觉观看转向感官的整体浸润开启了重要的方向。而浸润(或称沉浸),又与“交互性”密切相关,伴随着可触式界面在当代艺术实践中的广泛应用,在今天的新媒体艺术中交互性几乎成为了艺术作品中的必备属性。
本文的目的在于从20世纪50-60年代出发,在那些开创性的艺术实践中选取偶发艺术(Happenings)作为一个探讨的样本,将其与后来的新媒体艺术发展路径建立起一种结构性的联系,以期梳理出一条相对清晰的新媒体艺术发展的观念逻辑线索,展示出新媒体艺术发展历程中一个颇有意味的历史横断面。从更广阔的文化史角度来看,在这些早期前卫艺术实验的带领下,到20世纪60年代末,各种各样的新媒体技术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实验舞蹈和戏剧团体之中,并在此后大规模融入大众文化进入主流剧场、体育场、摇滚音乐演唱会、百老汇音乐舞台……从表面上看所有这些文化现象是一种自发的时代趋势,是大众文化与商业文化快速发展的结果,但从其来源看则是在早期前卫艺术实验的影响下,伴随着视觉优先的发展逻辑在被商业化快速消化和利用之后产生的增殖效应。
杜威、凯奇与偶发艺术的出现
大约在1949年,当时还在读书的阿伦·卡普罗(Allan Kaprow)一边阅读约翰·杜威的《艺术即经验》,一边在该书的页边空白处写下自己的思考和体会:“艺术与经验不可分离……什么是真正的经验?……环境是一种相互作用的过程。”约翰·杜威的著作对当时年轻的卡普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他后来的艺术观念奠定了基础,以下可略举一例来说明这种影响与联系。
在《艺术即经验》之中,当杜威讨论艺术的表现问题之时,他赞同塞缪尔·亚历山大谈论诗的观点:“艺术家的作品并非始于一个与艺术作品相对应的完成了的想象经验,而是始于一个对于题材的充满情感的刺激。……诗人的诗是由使他刺激的主题从他身上挤压出来的。”对此,杜威提出了四点理解:首先“真正的艺术作品是由来自一种有机体的与环境的状况与能量的相互作用的整体经验的建构。……第二点:所表现的事物是由客观事物施加在自然的刺激与倾向之上而从生产者那里挤压出来的……随之而来的是第三点。构成一件艺术品的表现行动是时间之中的构造,而不是瞬间的喷发。……它意味着,在时间之中,并通过一个媒介来进行的自我的表现,构成了艺术作品,这本身就是某种从自我中流溢出来的东西与客观条件的延时性相互作用,这是一个它们双方都取得它们先前不具有的形式和秩序的过程。……最后一点是,当对于题材的刺激深入时,它激发了来自先前经验的态度与意义。”【1】在杜威提出的上述几个观点之中,对于环境的强调、尤其是艺术作品作为行动与时间之中的构造、以及对经验的过程性的强调等观点为后来卡普罗形成自己的观点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从而构成了偶发艺术基本的理论逻辑出发点。
除了早期杜威的影响之外,跟随汉斯·霍夫曼学习的经历,让卡普罗开始接触到行动绘画,而行动绘画本身的特性也让他从一开始就走到了绘画的边缘,应该说,卡普罗后来的艺术创作也是从行动绘画的语言逻辑中开始展开的。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影响来自于约翰·凯奇。1957年,卡普罗参加了约翰·凯奇在社会研究新学校(NSSR)的学习班,正是这个班,促成了偶发艺术在纽约的诞生。约翰·凯奇是那个时代对当时的不少前卫艺术家都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他的思想来源比较多样化,既有早期达达主义的影响(尤其是杜尚),也有禅宗思想的启发,还有阿尔托关于剧场思想的感染,在这些思想的共同作用下,他通过一系列实验性演出活动开创了当代艺术在50年代初新的发展方向。
1952年,约翰·凯奇在黑山学院组织了一次表演《剧场表演1号》(也被简称为“事件”),这个作品经常被看作是偶发艺术的第一次先声。“事件”是这样展开的:面对一群观众,M.C.理查德和查尔斯·奥尔森各在一架梯子上朗诵自己的诗歌,现场有一张罗伯特·劳申柏的白色绘画悬挂在头顶,而他则在操控一架留声机播放着音乐。与此同时,迈尔斯·肯宁汉在观众座位间的空地上翩翩起舞,凯奇自己也坐在梯子上,有时读一段音乐与禅宗关系的讲稿,有时静静地聆听。【2】在“事件”中,凯奇设计了整个表演的过程和结构,但作品的实际发生和效果则是偶然的,当探讨这种结构设计的时候,他说:“我们应当考虑的结构是观众中每个人的结构。换句话说,观众中不同的人的意识会构成不同的经验,所以,我们越是少一点组织剧院现场,就像是对日常生活干预得越少,那么对观众中每一个人的结构能力的刺激就越大。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那么他们就会什么都做。”【3】由此可见,在这个作品中,凯奇所期望的并不是他的设计创造出了什么,而是通过这样的设计结构激发出了什么,在他看来,所激发出来的观众的那种体验性的结构,才是这个作品真正的意义。而在背后支持这一观点的,则是他对于艺术与日常生活之联系的理解:“通过日常生活中的观察,我试图发现人们在艺术中需要去做的那些事情。我认为日常生活是如此精彩,艺术将我们引入其中领略其卓越之处,感受得越多两者也愈加相似。”【4】在凯奇看来,艺术作品的卓越之处,在于激发日常生活中的那些灵感与认识,换句话说,艺术与生活之间的边界在凯奇那里被打破了,这一点,在卡普罗那里得到了直接的继承和进一步的发展。
在参加了凯奇的学习班之后,阿伦·卡普罗的思想也开始逐渐成熟,从1958年开始,他在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两个方面同时开始了自己的探索。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卡普罗的偶发艺术思想并不是从约翰·凯奇的那种实验表演中直接挪用过来的,这其中经过了一个经由绘画发生的转化,这就是对抽象表现主义的重新理解和评价。卡普罗对于抽象表现主义是非常熟悉的(这是他跟随汉斯·霍夫曼学习的重要成果),而同时又受到约翰·凯奇的思想影响,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开始引发他对于抽象表现主义艺术的重新思考,这个思考的契机便是对杰克逊·波洛克的重新讨论。
1958年,当纽约艺术界都在为杰克逊·波洛克的突然去世而哀悼之时,卡普罗在《艺术新闻》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波洛克的遗产》,文中指出波洛克的悲剧不在于英年早逝,而在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作品真正的价值,这种“盲目性”才是真的悲哀。在卡普罗看来,波洛克将绘画推向了真正的转折边界,在他之后留给艺术界的“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走波洛克的道路,对波洛克的美学稍加改变,不脱离、不过火,或许会创作出很多不错的‘类绘画’作品;另一个选择是彻底放弃绘画的制造,我指的是我们所熟悉的那种单一的平面化矩形或椭圆形艺术。”【5】在卡普罗的讨论中,他认为未来艺术的发展无疑是第二种选择方向,“在我看来,波洛克留给我们的重点是,我们必须关注乃至着迷于我们日常生活的空间和物品,无论是我们的身体、衣服、房间,还是(如果有必要)第42街的宽阔之特性,都值得关注。……每一种物品都是艺术家创作的材料……”对未来的艺术家而言,“生活的一切将为之开放。他们将在平凡事物之中发现平凡性的意义。”【6】至此,杜威对艺术与经验的理解、约翰·凯奇对艺术与日常生活之关系的理解,都在卡普罗那里得到了整合,而且他似乎还更为激进,主张彻底放弃传统的艺术形式,满怀激情地走向具有更广阔空间和更多可能性的日常生活。
实践与定义偶发
1958年,卡普罗在汉萨画廊进行了一次初步的尝试:他在展览空间中粘贴上各种各样的东西,收音机随机播放着声音,而他自己则随着声音在表演。很明显,这是对凯奇之前进行过的那些表演的一个略显生硬的简单模仿,但这不过他一系列尝试的一次小小的预演。1959年,卡普罗在鲁本画廊创作出了第一个公开的和完整的偶发艺术作品:《分为6部分的18个偶发事件》(18 Happenings in 6 parts),这是一个经过仔细构思和安排的活动项目,显示出了卡普罗对于行动绘画与凯奇剧场化表演的综合。
项目一开始,卡普罗对参与者宣称:“你们将在成为偶发事件的一部分的同时也体验到它们。”随后,这些参与者们每人收到了一个塑料信封,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东西:小纸片、照片、木头、描画过的碎片以及剪出来的数字。活动所在地鲁本画廊里有个两层的阁楼,用半透明的塑料墙分隔成三个房间,卡普罗事先提示参与者们:“有三个房间来完成这个作品,大小和感觉各不相同……有些人将在其中表演。”不同的房间中的椅子被摆成圆圈和矩形,以便让参观者朝向不同的方向,同时彩色的灯光又能透过这三个空间将其照亮。卡普罗在1号和2号房间中安装了全身镜,营造出一个复杂的视觉空间,而3号房间作为“控制室”装上了板条结构使表演者可以由此进出。每个参与者手中都有一个行为开展的计划和三张钉在一起的小卡片,上面写着“表演分为6个部分,每个部分包括3个同时发生的偶发事件,开始和结束均以铃声为号。表演结束将会响铃两声。”同时,提醒参观的观众要严格遵照如下提示:表演进行到第一和第二部分的时候他们可以坐在2号房间里,而第三和第四部分的时候他们将换到1号房间中,每次的转移也以铃声为号。不同部分之间间隔2分钟,“每一幕结束之后不要鼓掌,直到第六幕结束之后,如果愿意的话可以鼓掌。”活动开始之后,参与者们在临时搭建的房间之间形成的狭窄走廊里排成一列纵队,在一个房间中,一个女士站起来十秒钟,左臂举起,前臂指向地面,旁边的房间中播放着幻灯片。此后有两个表演者朗读着手中标语牌上的内容:“据说时间是本质……我们知道时间……精神上的……”;在另一个房间中,有人说:“我昨天就想要谈谈大家最珍视的话题:艺术……但我无法开始。”有人演奏着笛子、尤克里里琴和小提琴,画家们在安装在墙上的空白画布上作画,手推车上的留声机在播放着声音……最后,在18个同时发生的偶发事件持续了90分钟之后,4个9英尺长的卷轴从男女表演者之间的一根横杆上落下,与此同时,他们口中背诵着单调的词语:“但是……”、“然而……”然后,铃声响了两下宣告整个活动的结束。整个活动在正式开展之前精心排练了两周,而且是按照计划每天都进行排练,主要是参与者们要在卡普罗的指导下记住每个动作的顺序,以便使整个活动都处于精确的控制之中。【7】
卡普罗的这个作品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也显示出偶发艺术在诞生之初所具有的特点。首先,这个活动是经过精心设计和仔细准备的,卡普罗希望对整个活动的进程有细致的掌控,也就是说,整体结构是设定好的,不可控的地方在于在执行流程的那些过程中可能对参与者和观众引起的刺激,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个项目在结构上继承了凯奇的“事件”提出的核心诉求:提供一个能够刺激观众的结构;其次,与凯奇的“事件”不同的是,卡普罗在这个项目中发现了一些具体的差异,在谈到这个作品使用演员的情况时他说:他们“希望有明星角色。他们希望在大部分表演时间里说话,但是我在作品中采用极少的话语。我所建议的所有东西都跟他们的背景相悖……但是我所有的朋友,虽然不习惯于表演,却很有能力,因为他们感受到了他们绘画的来源。”【8】这里面显示出艺术家两个方面的设计诉求,一方面,通过减少话语,卡普罗试图尽可能地调动起人的体验;而另一方面,感受到“绘画的来源”显示出这个作品在设计的时候与行动绘画之间密切的关系,但是,此处的“绘画”从本质上来说却是反绘画的,也就是说,卡普罗注重的并非是作为名词的“绘画”,而是“绘画”这一行为本身以及由此带来的体验,以此来实现他在《波洛克的遗产》中所提出的对于行动绘画根本性的超越。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也是在卡普罗后来的艺术实践中一直发展的一点是:在这个作品中,通过一系列的指示和要求,观众成为了艺术家的道具,观看者成为了事件的参与者,在构成偶发事件的同时也达到了体验偶发的效果。
此后,卡普罗在整个60年代创作出了一系列偶发艺术作品,比较重要的有:《庭院》(Yard,1961年)、《词语》(Words,1962年)、《家庭》(Household,1964年)、《吃》(Eat,1964年)、《召集》(Calling,1965年)、《液体》(Fluids,1967年)等等,而且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从纽约艺术界开始,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偶发艺术创作风潮。比较知名的如:雷德·格鲁姆斯的《行走的人》、《燃烧的房子》和《神奇的火车旅行》(1959-60年)、吉姆·戴恩1960年的《微笑的工作者》、《杂耍行为》、克莱斯·奥登伯格的《射线枪剧院》(1960年)、《商店》(1961年)、罗伯特·惠特曼的《电影片段》(1968年)等等。但是,偶发艺术到底该如何定义?什么是典型的偶发艺术?在卡普罗不断进行艺术实践的同时,他也在不断撰写文章阐释偶发艺术的理论和思想。
在1961年撰写的首次系统介绍偶发艺术的文章《纽约的偶发艺术现场》中,卡普罗说:“偶发艺术就是单纯发生的事件。但是最好的偶发艺术有一个明确的效果,那就是我们能感到‘其中有些重要的东西’,它们似乎并不是往哪个方向发展,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文学指向。与过去的艺术相比,它们没有结构化的开端、中间或结尾。它们的形式是开放式的和流动性的。并不寻找什么明显的东西,因而也无所谓成功或失败,唯一确定的是:我们能够注意到不少平时没有注意到的东西在发生。它们为某个单一的表演而存在,或仅仅是少数几个,当新的偶发事件取而代之时,它们便永远消失了。”【9】在这段说明中,我们可以发现,卡普罗对偶发艺术早期的定义强调的是其偶然性和随机性,注重经验的引导与激发,在于意识到日常之中的日常性。但是伴随着艺术实践与思考的推进,卡普罗对于偶发艺术的认识也发生了拓展,一个典型的特点便是在1961年之后的作品中,对于作品结构与流程的精确掌控性不那么强了,而作品发生的空间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
在1966年的一篇类似于宣言般的文章《偶发已死:偶发万岁!》中,针对当时的质疑与批评,卡普罗对偶发艺术进行了一番辩护。他在文章中承认偶发艺术正面临着不少质疑,甚至有人宣称,早在1958年,偶发艺术从一出现就死亡了。但卡普罗认为,偶发艺术是今天唯一的地下前卫,它不仅没有消亡,反而像慢性病毒一样传遍了全世界,他举例说目前有超过40位男女艺术家在从事偶发艺术的创作,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如:日本、荷兰、捷克斯洛伐克、丹麦、法国、阿根廷、瑞典、德国、西班牙、奥地利、冰岛和美国,接着,卡普罗还列出了一长串艺术家和作品的名字,主要是1963-66年间与偶发艺术相关的艺术创作。但如何延续偶发艺术?卡普罗提出的第一条就是:“偶发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应该保持模糊,而且或许应该尽可能地模糊。”【10】与早期作品中那种明显的剧场化表演模式相比,此时的卡普罗已经开始将偶发艺术向更为广阔的日常生活中拓展,力图实现艺术作品在日常生活之中的“渗透”。
在1967年的文章《精确定位偶发》中卡普罗又对偶发艺术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说明和分类,他列举了六种偶发艺术的类型:第一种风格如:夜店、斗鸡或袖珍戏剧风格的偶发;第二种风格如娱乐表演的偶发;第三种风格是事件的偶发;第四种风格如导游参观或花衣笛手(Pied Piper)式的偶发;第五种风格基本是精神性的,比如一个想法(Idea),或以普通形式及笔记写下的书面表达;第六种风格是行动式的偶发。它直接进入日常世界之中,忽略剧场和观众,注重行动超过注重冥想,行动的偶发对情境进行选择和结合,使之能够参与其中,而不是观看或仅仅思考。【11】在这篇文章中,卡普罗把之前进行过的偶发艺术实践所涉及到的可能都考虑了进去,并且又更进一步,从特定的空间(剧场)、到开放的空间(室外)、到简单的活动、思考以及行动都可以成为偶发艺术出现的情境。
但是,就在偶发艺术拓展的范围在变得愈加广阔之时,偶发艺术自身的问题也变得愈加明显了。在后来的不少研究者看来,偶发艺术在整个当代艺术史的进程中似乎显得并不那么重要。比如,针对那种狂欢或杂耍式的活动现场,有学者这样评论偶发艺术:偶发艺术根植于两个看起来似乎并不相关的趣味:(1)试图把一条市中心街道全部的“信息复杂性”带入一个狂欢空间;(2)玩弄知觉的模式。【12】 “偶发艺术回顾起来可能没有它们当初发生时那么重要。到了1962年,整个现象已经变得太商业化,根据奥登伯格讲的‘人们乘凯迪拉克到来’,因此,除了卡普罗,主要艺术家全都回归到绘画和雕塑,或转到电视和电影。”【13】偶发艺术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主要在于三个方面:其一在于活动本身的娱乐化效应,参与者试图过把演员的瘾,而参观者大多是凑个热闹乐在其中,但激情过后人们是否真的愿意去了解卡普罗的那些理论主张,思考偶发艺术带给当代艺术创作的意义是值得怀疑的;其二在于偶发艺术激进地模糊了艺术与生活之间的边界使之陷入到了虚无主义的境地,对于一般的观众甚至大多数艺术从业人员而言,艺术作品最好是一个能够看得见摸得着、能够加以清晰界定的东西,而偶发艺术在当时除了热闹的活动之外,并无其他可以明显直接加以发展和继承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它陷入了与早期的达达主义类似的虚无主义困境;第三点与第二点相关,偶发艺术是融合了行为、表演、环境等多种因素在内的艺术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体制批判的色彩(这里需要区分的是:作为艺术运动的“体制批判”直到1960年代末才出现),其反博物馆、画廊和收藏机制的特性使得不少艺术家在进行过一段尝试之后便很快回到了传统的绘画与雕塑创作之中,比如前述偶发艺术的热情参与者吉姆·戴恩、克莱斯·奥登伯格等人都很快转向了利于出售和收藏的绘画和雕塑创作,这也是偶发艺术在热情过后迅速消退的一个主要原因。
但是,当我们今天重新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偶发艺术并非如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不那么重要,也并非所有的艺术家都放弃了偶发艺术的实验,当早期的偶发艺术参与者们转向传统艺术媒介之后,新一代的艺术家也开始了新的偶发艺术实践,尤其是当我们重新梳理新媒体艺术发展的线索之时,我们会发现恰好是1960年代兴起的偶发艺术给当时的年轻艺术家们提供了一个实验的场所和语境,当新的技术与当代艺术实践相遇之时,便诞生出了新媒体艺术发展早期不少重要的艺术作品,尽管这些探索并不都是一直延续下去的,有的艺术家也只是在一段时间从事这样的实验,但是他们共同为未来的艺术发展方向打开了新的探索空间。
偶发艺术的新媒体实验
偶发艺术从一开始就具有开放与包容的特性,它将行为、物品与环境进行了大胆的融合,这一特性让新的技术能够在前卫艺术实践中被迅速使用,进而在使用的过程中得到快速的发展。以1959年的《分为6部分的18个偶发事件》为例,从形式上来看这个作品具有的重要开创性意义就在于将行为、声音、光线、影像、物品、表演者、观众等等融合在了一起,作为构成作品整体的部分,这种方式创造出了一种非常独特和震撼的效果,因此,伴随着卡普罗个人艺术实践的发展和理论阐释,他影响了当时的一大批艺术家利用各种各样的设备和媒体进行偶发艺术的实践。除此之外,阿伦·卡普罗在艺术实践中对新技术也持有一种乐观和开放的态度,他从根本上将其看作一种以日常生活为源泉的真正的参与性艺术的理论化模型,隐喻了反馈(feedback)与交互(interactivity)。【14】正是在偶发艺术的开放式结构中,提供了一种让参与者和观众能够“浸润”其中的机会和实验的可能,当以控制论为基础的计算机技术开始大量应用到艺术创作中之时,反馈与交互这两个概念,成为了后来的新媒体艺术创作中非常重要的概念。以下略举几位艺术家的作品来说明当时所开展的这种重要的开创性的实验。
尽管卡洛琳·施尼曼(Carolee Schneemann)一直是作为女性主义行为艺术家而备受关注,但她1960年代的那些作品多少都带有偶发艺术的影子,这与她在1960年代初结识并受到阿伦·卡普罗的影响密切相关,创作于1964年的《肉的快乐》就带有典型的偶发艺术的特点,所不同的是艺术家强化了狂欢式活动与肉欲的感觉。施尼曼1967年的作品《雪》是新媒体艺术史上经常提到的重要作品,在这件作品中,艺术家采用了大量的媒体设备,创造出了一种非常震撼的偶发艺术现场。但是,与偶发艺术普遍具有的无目的性(或有意模糊目的性的)特点不太一致的是,这件作品又有着相对明确的主题诉求:对越南战争的反思,根据施尼曼自己的说法,作品创作的初衷来自对越南战争的暴行所感到的愤怒和悲伤。在纽约马提尼克剧院,艺术家布置了一个颇为迷幻的舞台环境:有彩色灯板、电影放映机、幻灯机、频闪灯、撕碎的拼贴画、挂起来的彩色水袋、老树枝、绳索、金属箔片、泡沫等等。在观众的座位区,艺术家和工程师随机选取了几个座位,在座位下面装上麦克风,麦克风捕捉到的声音信号可以传输到一个整流器切换系统,而这个系统又与现场的媒体装置开关相连,由此,座位上观众随机发出的声响都能够控制和影响(从而也是参与)现场的媒体元素。作品开始的时候,电影、幻灯机开始放映图像,与此同时,8个不同种族的表演者在现场表演侵略者和受害者、施虐者和被害人、追求爱的人与被爱的人,或者就在这个综合媒介的电影氛围中简单地呈现自我。这场表演共包括5个电影,以其中一个名为《越南片》(Viet-Flakes)的电影为核心,从内容上构成了冬天的环境与越南战争暴行的图像并置与情境营造。从结构上看,作品本身还是剧场化的,还是传统的观看与表演的模式,但是通过借助声音传输与控制设备,施尼曼却在事实上让观众参与到了作品最终的实现效果之中。一方面,通过座位底下的声音控制系统,观众成为了整个现场环境的控制者,实现了偶发的现场效果;而另一方面,观众也不仅仅是一个外在观看者,表演现场的氛围营造出的是一种整体性的沉浸式体验,由此也将他们带入到了越战的现场,成为了亲历者和见证者,可以想见,整个作品的现场体验是颇为真切与压抑的。
与施尼曼类似,在阿伦·卡普罗的影响下,当时年轻的阿根廷裔女艺术家玛塔·米努辛(Marta Minujín)也是新媒体偶发艺术的重要实践者之一,米努辛早在1963年就开始创作偶发艺术作品。1966年,米努辛与阿兰·卡普罗及沃尔夫·沃斯泰尔(Wolf Vostell)策划举办一个宏大的偶发艺术项目《三个国家的偶发》,计划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美国纽约和德国科隆同时进行,作为这个作品的组成部分,米努辛于1966年10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策划完成了《同时性的同时性》(Simultaneity in Simultaneity)。艺术家将这个作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名为“瞬间入侵”,在10月24日星期一由广播、电视、电话和电报同时播送一个事件:事先挑选好120个人,到他们家中拍照、拍摄和录制,造成他们被媒体“入侵”的效果。按照米努辛的说法,他们当了十分钟“通讯媒体的俘虏”;第二阶段名为“覆盖同时性”,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托尔夸托·迪·特拉学院分两次完成。首先于10月13日周四,米努辛从当地文化和新闻界邀请了60位名人,当他们坐在一台带晶体管收音机的电视机前的时候,给他们拍摄和录像。当他们走出去的时候,每个人都要谈谈对这个事件的看法以及对媒体整体的看法。11天之后,还是这60位名人又回到学院,当他们回到各自的座位前坐下后,能够在电视机屏幕上和幻灯机投出的图像中看到自己:他们的形象、姿势和动作,同时还能通过收音机听到自己的声音。米努辛的这个作品构成了一个颇具影响力的社会媒体事件,而且其包括的人不仅仅是受邀的作品参与者,在她设计和安排数百人进行媒体播放的时候,社会公众都可以在电视机前调频到相应的节目中去观看,在将更多人纳入到这个偶发艺术活动之中的同时,也验证了媒体的强大力量:对日常生活实现了全面的入侵和控制,而这在今天已成为现实。
与之类似的作品还有1967年的《回路》,同样也是借助大众媒体、计算机调动社会公众参与的大型偶发艺术活动。1967年米努辛应邀参加蒙特利尔世界博览会,恰逢加拿大联邦100周年纪念。4月28日,她在青年馆展出了作品《回路》。6天前,蒙特利尔的报纸刊发了一份调查问卷(包括:姓名、性别、身高、体重、头发、嘴巴、眼睛、心情、装扮),对米努辛的作品感兴趣的人可以在4月25日之前填写好调查问卷并发送给艺术家。收到反馈回来的调查问卷之后,艺术家用一台计算机处理了这些回复,根据回复的相似特征将其分成了三组参与者,艺术家规定只有那些回答了问卷的人才能够参加作品《回路》的现场活动。参加者们被要求带好便携式收音机在下午5:30到青年馆大门口集合。第一组参与者被指示去展馆的礼堂,第二组被指示去了一个名为“集市”(Agora)的地方,而第三组则在剧院入口处排成一列纵队。在礼堂的参与者们能够同时从不同媒体中看到图像:在一个放大的电视投影上看到他们自己的情况、礼堂入口处排队的第三组的情况。“直播”由位于礼堂观众座位前方的六台监视器来传送信息,青年馆外的情况则用投影仪投射在墙上,此时,在舞台上的三个大屏幕播放着奥森·威尔斯的《公民凯恩》以及蝙蝠侠系列的一段情节。这一体验的目的是为了比较不同媒体的不同时间。参与者们通过他们的便携式收音机,能够听到自己说话和发出的声音,第三组也同样可以,还可以在两个指定的频道间进行切换。通过礼堂里面的几个扬声器,还能够让里面的人听到第三组的情况。在一个活动平台上,另有8个参与者观看了前一天录制的录像带。在礼堂的座位中还放置了40台电视机,在不同的频道上播放。到6点钟的时候,参与者们被要求转动电视机的旋钮,调到指定的频道,以便看到超外差(Superheterodyne)。在“集市”的第二组参与者也观看了其他组的情况。第三组人仅仅通过放大的投影画面、音箱和收音机来追踪发生在剧场中的活动,他们用宝丽来拍摄的自己的形象则用投影投在外墙上。当一场体验完成之后,每个小组与另一个小组交换场地,并重新开始新一轮的体验,由此完成“回路”。这个作品引用了通信技术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术语“超外差”,本来是指在通信收发机中广泛使用的一种结构,超外差收发机在工作的时候需要将从天线接收的信号与本地振荡器产生的信号一起输入到非线性器件(混频器或者变频器)中得到中频信号,在这个过程中频率会发生多次的搬移,因此也需要有不少“中介”,比如可以有多个中频频率和中频模块。这个作品通过设计一场复杂的活动来“模拟”通信信号的收发路径问题,虽然过程略显复杂,但整体而言还是显示出了艺术家对媒体介入日常生活的关注,探讨了在信息的制造、传播和接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在新媒体艺术发展历程中,还有一位重要的艺术家杰弗里·肖(邵志飞)(Jeffrey Shaw)早期的艺术实践也是从偶发艺术开始的。杰弗里·肖早期的作品就显示出对于电影的关注,1966年的《连续形式的出现》就是以偶发艺术的形式探索如何将电影形象延伸到观众空间中的方法,但就电影空间的突破而言,1967年的《电影电影》更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它探索了对于常规视觉观看经验和幻觉空间边界的突破。这个作品是专门为在比利时诺克勒组特(Knokke-le-zoute)举办的实验电影节所做的扩展电影表演,由杰弗里·肖、西奥·博特斯奇沃(Theo Botschuijver)和肖恩·维尔兹利-米勒(Sean Wellesley-Miller)合作完成。表演开始时,他们先在场地上布置好一个巨大的可充气结构,这是一个圆锥体,由外部透明膜和白色的内表面组成,充好气之后,将电影、幻灯片和光效投影在其表面。通过这种结构,艺术家将平面化的电影屏幕转化成了一个三维的活动结构,观众也不仅仅是坐在椅子上观看,而是邀请他们直接跳到这个“屏幕”之中去参与互动,现场气氛热烈,甚至有人自发地脱掉了衣服,进行裸体的狂欢。伴随着观众在其中的活动,整个“屏幕”成为了一个互动的空间,一方面人的活动并没有事先的安排,是任意的,同时人的活动也在不断地改变着这个软体的充气结构,从而造成了投影影像的不断位移和变形,生成偶然性的视觉效果;另一方面,真实的场景与投影下来的虚拟场景融为了一体,实现了现实与虚拟的一体化融合,带来了视觉与感觉的沉浸式体验,在今天看来,它预示了当代数字化互动产业的发展方向。
偶发艺术的出现,是20世纪50年代纽约艺术世界中反形式主义倾向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但其对艺术经验的激进推进却是始料未及的。杜威将艺术定义为经验,指向的是日常生活的审美;而卡普罗对杜威观念的推进,在于将艺术定义为参与性的经验的同时,也将对于有意义的经验的判断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实验性语境之中,其成果是开放且不可预见性的。新媒体技术与偶发艺术的相遇既是历史的偶然也是必然,没有偶发艺术对于艺术经验的打破和开放式实验,新媒体技术直接介入当代艺术创作可能还会略有波折,诸如交互、沉浸等概念或许还需要从其他艺术实践中寻得;而没有新媒体技术的介入,偶发艺术对于经验的推进可能是也有限的,从今天的视角来看,或许其在艺术史上的地位还将停留在曾经的判断:不过是一段时间的热闹。杜威在《艺术即经验》中提出:要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理想化的性质。也许这一观点不仅对艺术的发展有所启示,对于理解历史亦是如此。
注:
【1】(美)约翰·杜威:《艺术即经验》,高建平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8月第1版,第69-70页。
【2】John Cage, Michael Kirby and Richard Schechner: "An Interview with John Cage", The Tulane Drama
Review, Vol. 10, No. 2 (Winter, 1965), pp. 52-73.
【3】Ibid, p. 55.
【4】Ibid.
【5】“The Legacy of Jackson Pollock”, in Allan Kaprow: Essays on the blurring of art and life,
edited by Jeff Kel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7.
【6】同上,P.9.
【7】RoseLee Goldberg: Performance Art: From Futurism to the Present, Thames and Hudson, 1988, pp.128-130.
【8】Allan Kaprow, cited in Michael Kirby, Happenings: An Illustrated Anthology, New York: E.P.Dutton,
1965, P48.
【9】“Happenings in the New York Scene”, in Allan Kaprow: Essays on the blurring of art and life,
edited by Jeff Kel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p.16-17.
【10】“The Happenings Are Dead: Long Live the Happenings!”, in Allan Kaprow: Essays on the blurring
of art and life, edited by Jeff Kel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p.62.
【11】“Pinpointing Happenings”, in Allan Kaprow: Essays on the blurring of art and life, edited by
Jeff Kel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p.84-89.
【12】Richard Schechner: “HAPPENINGS”, in Happenings and Other Acts, Edited by Mariellen R. Sandford,
Routledge, 2005, P.181.
【13】(美)乔纳森·费恩伯格:《艺术史:1940年至今天》,陈颖、姚岚、郑念缇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4月第1版,第196页。
【14】Allan Kaprow: Essays on the blurring of art and life, edited by Jeff Kel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XIV.
赵炎 博士 中央美术学院助理研究员 《世界美术》编辑 100102
(本文原载:《世界美术》,2018年第1期。)